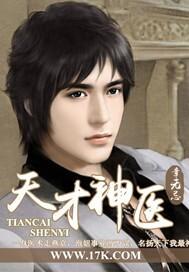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明月照我作者 > 第127页(第1页)
第127页(第1页)
崔少东家捡起脚下的一捆火药,端在怀里。谢慈摁着芙蕖却始终没有动作。三娘怀中也抱上了一捆,左摇右闪,才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身上已经挂了几道伤。不是猛虎抓的。这样体格的老虎一巴掌上去断然不会给她再起身的余地,是她自己在地上狼狈摔滚的擦伤。崔少东家托着手中的火药,忽然觉得黏腻的手感不对劲。他捻着手指,低头一看,当场疯了:“贱人啊──用水泡的火药,你打量糊弄谁呢!?”三娘好不容易回到他身边,一愣:“什么?”她不可置信地低头一看,顿时绝望漫上了心头,她早早准备好的这一批火药,不仅被水泡了个透彻,而且并非一两日之功,她摸上去心里就有数了。三娘:“是谁?!”猛虎再扑过来的时候,身心俱疲的三娘再也无力躲闪,身体抽动了一下。绝望之际,不知她有没有遗憾过终此一生的算计,最终落了个葬身虎腹的下场。芙蕖甩开宽袖,一连三枚玲珑骰子接连钉进了那畜生的左眼里。猛虎吃痛,脑袋甩像一侧,撞到了墙壁。三娘迟钝的手脚并用爬出来。芙蕖趁机拉了她一把,说:“给我名单,我救你。”三娘:“什么名单?”芙蕖:“崔大掌柜的手中名单,我知道你有。”三娘一咬牙:“我给。”芙蕖:“现在。”三娘惊愕道:“你疯了,我怎么可能随身带着?”芙蕖丝毫不肯让步,死死的拉着她:“就现在,让我见到实在的东西,我救你出去。”趁火打劫务必不能给对方留反悔的机会。芙蕖料定她一定会给。因为方才凭借她的观察,三娘在逃命途中,可是想都没想,就扔下了她的老父亲。还以为多孝顺呢。老虎面前,原形毕露。那畜生被芙蕖戳瞎了一只眼,虽然暂时阻止了它的攻势,却更加激发了它的兽性,它的下一步反扑会更激烈。芙蕖与三娘对峙上了。但是那畜生不会等着她们商量完了再扑咬。谢慈头一偏,静默的目光放在了崔少东家身上。崔少东家从嗓子里发出一声惊恐的呜咽,退后的几步,警惕的盯着他。谢慈的刀不在身边,随身只有一把袖珍的匕首,但也足够,他朝着崔少东家走去。崔少东家眼见三娘已拿出东西交换自己的性命,他慌不择言道:“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只要我有我都能给你,别……”谢慈冷笑:“没有什么比你的命更能打动我了。”崔少东家应该庆幸,谢慈没有机会真正见到那些千姿百态的蜡人,否则他现在的下场一定比葬身虎腹更要惨。猛虎与谢慈几乎是同时动身。崔少东家后颈上干涸的血迹已经无法吸引老虎的注意了。谢慈的匕首斜刺向崔少东家,而猛虎的爪子落在谢慈方才站立的地方,扑了个空,立时转身,继续追上去。崔少东家只见到那骇人的一幕,手无寸铁,行止笨重,慌张之下,还来不及抱头鼠窜,便眼睁睁看到谢慈那苍白修长的手指握着一截不足三寸长的锋刃,在他的腹部活生生撕开一道口子。喷溅而出的鲜血让逼仄的甬道中溢满了浓郁的血腥,那比谢慈身上那若有若无的味道更能刺激到猛虎的鼻子。三娘目眦尽裂,愕然看着这一切。在三娘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芙蕖和她是差不多的表情。猛虎落地,一掌拍烂了他的脑袋,白色乳状的脑浆整个飞出来,摔在墙壁上,像鱼泡一样,啪叽碎了,顺着凹凸的墙壁淌落。崔少东家的尖叫卡在喉咙中,戛然而止,猛虎尖利的爪子彻底剖开了他的腹部,撕烂了他的身体。芙蕖不可置信的望着那一地的狼藉。谢慈搁在她的眼前,其实并不能挡住什么。芙蕖嘴上嚷嚷着要这个死要那个死,都是停在嘴上而已。纵然崔少东家该死,罪不容诛,也不该私刑处置。倒不是迂腐。而是他的所作所为理应张布于光天化日之下,顺民意而处置。芙蕖盯着他的背影,似乎要在他身上烧出一个洞来,看上去那么冷静,理智都喂进狗肚子里去了。三娘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她没有哪一刻比现在更想活下去,身侧站着的两个同伴是随时伸手就能将她推进深渊的人,但也是她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三娘哆嗦着双手去拉芙蕖的手臂:“我给你,名单是吧,我现在就给!”芙蕖便见着她开始解衣服。一层一层的解下来,露出了雪白缎子的寝衣,已经莹润白皙的肩膀,脖子上挂着红绸肚兜,她测身,一把将其扯下来,又层层裹上了衣裳。肚兜上余留着她的体温。三娘将东西塞进了芙蕖的手里,生怕她不收似的。芙蕖手掌一松,瞧见她肚兜的内侧,用银线密密麻麻绣满了名字。是崔字号地下银庄这些年来进出走账的完整名单,她果然贴身带在身上。芙蕖当即信守承诺,答应她:“跟在我们身边。”谢慈见她拿定了主意,二话不说,收了匕首,经过她们身边,撂下一句:“跟我走。”崔少东家滚了一只浑浊的眼珠子在外面,了无生息地注视着这一切。老虎扑杀活物并不是因为腹中饥饿,它撕烂了人的残肢,但却不吞食,只是甩在一边,便开始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他们快步在甬道中穿行,又回到了那条遍地横尸的路上。地上的尸体成了最好的掩护。谢慈时不时回身踢过去几具,阻拦那畜生追来的脚步。崔少东家原本的属下,以及困在地下的工匠们,都被冲散了。谢慈一路上有遇见零星几个人,他们六神无主之下,自然而然的就跟在了谢慈的身后。而其余人听到了动静,也慢慢涌了上来。工匠们手中有铸币用的工具。一股脑的砸在路上,也掀翻了堆成山的铜币。他们一路折回到山间的主墓室。谢慈飞身跃上正中供奉着棺椁的石台,一掌将沉重的棺盖推开了一半。“有火药,来人搬。”芙蕖凑上前去一看,惊奇道:“哪里弄来的?”棺椁的主人已经被谢慈折腾的不成样子。芙蕖闭了下眼睛,看到里面确实攒了几捆火药。谢慈解释了一句:“火药是半个多月前泡的,但为了掩人耳目,箱子最外层保存了完好,在今日事发之前,我临时挪到这里了。”主墓室的门一关,猛虎在外徘徊了一阵,开始用头撞门。几个身强力壮的工匠怀抱了火药,便要往那边去跟猛虎拼命。谢慈刚与芙蕖解释完,便对着他们骂道:“蠢东西,去炸开出口。”即便倾尽全力弄死了作乱的老虎,可他们人困在底下,终免不了一死。谢慈所藏下的那一点微薄的炸药,杀伤力虽不足以撼动整个地下密道,但若想炸开一道石门,是有十足胜算的。轰然炸响。山间草木为之震颤。谢慈踢开了碎石,钻出洞口,眺目山野间一片寂静。这很不寻常。他带来的人仿佛都死了一样,闹出如此大的动静,也不见人影。芙蕖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刚踏出洞口,她鼻尖一嗅,忽然抬手捂住了口鼻,急切道:“闭气!”几乎是在她话音刚落下,谢慈便感觉到了瞬息的眩晕。此时,面前炸开山石的烟尘终于散开,而后续番外整理在滋,源峮无耳思酒零八伊玖二面前却仍是雾蒙蒙的一片,像是老天爷忽然下了雾,但这雾气异常,在这初冬草木凋零的时节,正当午时的阳光也驱不散。谢慈:“是什么?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