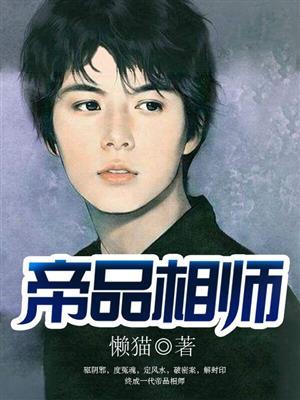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皆有尽时 > 第287章 听到看到(第1页)
第287章 听到看到(第1页)
葛玥童到的时候,陈言和虞移都没在病房,一进门生活管家正在打扫卫生更换床品全屋消毒什么的,看到葛玥童来了打了个招呼说好些天没见了。
就一个周末,葛玥童带的东西不多,一个书包一个手提纸袋,她把东西放在茶几上,一边和生活管家闲聊一边先去接了杯水,前城的天和迎城一样热,推开自己之前住的那间房,收拾的很是干净整齐,她也知道这次来她用不着住这里了,所以就没把东西提进来。
虞移陪着陈言去做康复了,这边的生活管家会理发刮胡子,虞移说这两天陈言的胡子长了很沧桑,等下他们练完了去刮个胡子就回来。
葛玥童正在和齐叔发微信,说因为虞移要去找工作,她已经回到前城照看陈言了,周一没课,她下周二一早就回去。
齐叔估计这会儿不算忙,很快就回了信息,说既然葛玥童回来了有件事也好办点。
陈言受伤的事情最后还是没能瞒得住爷爷,老爷子今年快九十了,除了腿脚不比以前方便能到处走动走动,眼不花耳不聋,脑子也清楚,一开始陈言出事,村里说什的都有,毕竟救护消防和警察一晚上都来了这件事不假,姑姑姑父知道了也都担心的不行,但是又不敢表现出来,怕爷爷知道了要着急,姑姑倒是跟齐叔打听过几次,知道陈言是真的受伤住院了,还说要去医院看看,齐叔给婉拒了。
当时正赶上五一假期,姑姑的儿子难得休息带上媳妇回来了,一家人开着车出去周边旅游了好几天,烧鹅店也干脆店休,正好把村里传谣言传的最热闹的那一阵子给错过去了,假期结束姑姑的儿子走没两天,爷爷说总是头晕不太舒服,上医院一看血压高起来了,医生说这个岁数了留院观察一下,爷爷就也在医院住了差不多一周才出来。
姑姑姑父倒是一直都很关心陈言的伤情,只是一边照顾老人一边还要管店,确实分不开身,就听齐叔的一直也没来看望,两口子本以为爷爷出院的时候村里的流言也就过去了,平息了,大家也就假装不知道,瞒着老爷子。
本来也就真的这样平安无事过了好多天,谁知道有天下午几个食客在店里吃饭高谈阔论的时候,不知怎么就又提起来这件事了,可能是喝了点酒嗓门儿也大,而且说的玄乎其玄,说什么陈言的腿都被砍掉了,手指头也被剁掉了好几根扔在半山腰上了,警察大半夜的打着手电下去捡,当时姑父正在清理锅灶洗洗涮涮准备收档,姑姑去楼顶查看积水情况了,谁也没注意这些人在聊什么。
爷爷本来嫌天热好几天没白天下楼了,那天正好大中午一场暴雨傍晚凉风习习,爷爷正坐在店门口的抱着猫咪看晚霞,一听到什么桦林制衣的小陈出事了,放下猫咪就跑进来问,这帮人喝了点酒口无遮拦的,把爷爷当成了来听热闹的好事者,更是绘声绘色添油加醋的又讲了一遍,爷爷听到这个消息差点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好在这帮人虽然嘴巴上没个把门的,人还不坏,靠得近的一个人眼疾手快一把把爷爷给搀扶住了,几个人都围上来问老人家你没事吧,姑父才听到了不对劲,跑出来一看爷爷脸色就不好,赶紧问怎么回事,食客里有个人就说我们没做什么啊,你们家老爷子自己要来打听桦林小陈的那个事儿啊,你看就成这样了,和我们可没关系啊。
姑父一听这话脑子也嗡了一下,赶紧把爷爷搀扶到椅子上坐下,食客们一看这情形酒也不喝了,赶紧买单走人,姑姑听到姑父喊她,赶紧从楼上下来,一看这情形都明白八分,心里虽然也有点埋怨这些食客们什么都要议论,可也知道这事情估计早晚得露馅儿,看爷爷的脸色很不好,姑姑张罗着让姑父赶紧带上爷爷上医院,一路上爷爷都没说一句话,到了医院才知道姑姑姑父不是带他来看陈言的,一向脾气很温和的老人发了很大的火,姑姑姑父连带着要给量血压的护士跟着劝了好一会儿,爷爷才平静下来,量了个血压,又高上去了,在急诊科留观了一晚上,一晚上都在要求上医院去看陈言,姑姑姑父怎么解释说陈言并没有伤成那样都没用。
那时候陈言已经被向激川转院走了,况且陈言具体住在哪个医院的消息其实本来也是有意不公布的,姑姑姑父眼看着爷爷根本劝不动,只能找齐叔,第二天爷爷出院回家,齐叔忙完厂里的事午饭随便扒拉了一下赶到烧鹅店门口等了。
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无论齐叔怎么和爷爷解释陈言手脚绝对健全只是现在还不太适合探望,爷爷都是不听,情绪上来了谁说也不听,看那个血压好像又高起来了,齐叔心里真的是不好受,他也知道比起缺胳膊少腿,对于陈言的这些亲友来说,他脑子坏了才是更难以接受的,这也是他迟迟不愿意同意让陈言的爷爷来见一面的原因,他怕老爷子接受不了这个大的刺激,别到时候小的没好老的也倒了,那可真的是乱套,所以就一直劝着爷爷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爷爷一看此路不通,当时也就没再表态,姑姑姑父以为是把爷爷说通了,总算松了口气,谁知道爷爷中午趁着姑姑姑父在忙直接就自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没问出个所以然不说,这么大年纪了大中午跑过来,把民警们紧张的够呛,赶紧联系村干部让家属来领人,爷爷被领回家以后,倒是没再出来找,但是也不怎么吃东西了,姑姑姑父这一看老爷子是要搞绝食抗争,又赶紧找齐叔想办法,齐叔思来想去要不就等陈言休息的时候带老爷子去见一面,见了就说在睡觉呢,想来老爷子也不会惊动陈言,只要让老爷子能看到陈言全须全有的应该问题就不大,况且陈言住院的环境这么好,老爷子应该能放心了吧。
既然要等陈言休息了再来,就得和陪护的虞移串通好,说实话齐叔对虞移还不是很放心,总感觉小伙子看上去有点神经兮兮的不靠谱,正在发愁这工作要怎么开展,葛玥童就打电话说她已经回来了。
虞移说陈言的生物钟已经恢复的和以前差不多了,所以最后大家决定周六中午陈言午睡的时候带爷爷过来看一看,陈言受伤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剃掉的头发也长出了短短的头发茬,看着比没头发的时候没那么吓人了,也比有头发的时候精神了不少。
知道明天中午就可以去医院看陈言了,爷爷才总算是平静了下来,也开始正常吃饭了,这让姑姑姑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厂里最近在加班加点的赶制华城商砼和艾星集团订单,所有人都忙得上火,小姚嘴巴也烂了好几天了,借了梁梦芸的玻璃壶在办公室煮凉茶,搞得一整个办公楼都是一股又苦又香的凉茶味儿,因为陈言住院,厂里仓库干活的只剩胖子一个老员工,齐叔找了个临时班的叉车司机,技术还行,但是就是多余的活儿一点点都不肯干,只开叉车,搬运调整这些都得另外找人做,小姚和小张最近有空了就在仓库帮忙,这个临时的叉车司机还真是不客气,脸难看说话也不好听,要不是临时再没有合适的人了,谁也不想跟他搭班子干活。
“你这也太养生了吧,”去仓库帮忙回来的路上,小张远远地就闻到了那股凉茶味儿,一边擦汗一边说,“不过等下回去给我也来一杯,我感觉我的火都上来了,真的是受不了这个狗司机了,说话那么难听。”
“哎,怎么这太阳都快下山了还这么热啊,要了命了,你说小陈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好想他啊,”小姚比小张要瘦一点,干点体力活也是累的全身湿透,“现在仓库我们四个人都干得这么累,以前只有小陈哥和胖子就能干的好好的,别的不说,小陈哥真的是好适合做同事,人好好,还会干活儿,你说宋总也是真的很奇怪了,小陈哥出这么大事儿,到现在都没说要组织我们去看一看的,总不能是董总不让去的吧,我听梁姐说小陈哥这种算工伤,厂里可能要赔不少钱呢,但是这也是应该的呀,要不是为了这个厂,小陈哥有病么大半夜跑来巡什么逻,而且自从上次团建董总扣着小陈哥不让去,我就感觉董总这个人好冷血,小陈哥在这给他干了十多年了,一出事儿就这么的不闻不问。”
“是不是董总的意思真不好说,”小张不由得有些心虚,毕竟董总被打成那个样子估计一时半会儿也做不了什么决策了,况且这情况让宋总怎么组织大家去看呢,自己去了一趟就把这马甲给撞破了,一群人乌央乌央围过去,这不就是给董总开介绍会呢,“不过我总感觉宋总不让去我们就还是听他的比较好,毕竟领导总是知道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况且我听说当时小陈哥倒在仓库里满地都是血,伤这么重不得养他三五个月的啊。”
“也是,”小姚叹了一口气,“不敢想,你一说我都感觉疼死了,你说这混蛋怎么这么缺德,伪装成客户跑来厂里踩点,我们厂有什么东西让他这么惦记的,钱也没有,机器设备搬不走,仓库当时为了来货都清空了,有什么好踩点这么久的,不会真的像我在村口快递站听说的,小陈哥是董总混黑道金盆洗手以前的打手吧,听说以前就不是什么善茬,听说咱们厂子建厂之前很多要不回来的债都是他去追的,手段很厉害,这次被人家寻仇了,我就说总感觉小陈哥那个人看上去就是个挺厉害的人,没理由就在我们桦林这个小地方一待待十多年啊,你说这些不会都是真的吧?”
“别胡说了你,”小张感觉那个真相就要冲破自己的嘴巴,但是一想到齐叔那张严肃的脸,赶紧把嘴里的话给咽了回去,还好已经走进办公楼了,太阳晒不到的地方多少还带这些阴凉,小张赶紧转移话题,“哇塞这里总算凉快多了,真快啊,明天都周六了,去年五月份也是过完五一就一天没休息,几乎是一口气干到端午节了,今年这个订单量这么大,感觉六月份都不一定有的休息了。”
虞移买的是周五晚上最晚一班的动车票,他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不着急走,听葛玥童说秦老师让小修小改一下开题报告,又赶紧让葛玥童现在就把文档打开,看了看秦老师的修改意见,虞移表示这还真的是文科思维和理科思维有所差别,让葛玥童听秦老师的稍微改下问题应该就不大了。
陈言晚上吃了点烩面片,他最近勺子用的还行了,也能自己扶着器械站起来了,这会儿吃完饭又睡着了,虞移把病房的门关上了,时间还早,拉着葛玥童瞎聊天。
“学长现在一天能睡十七八个小时的感觉,”虞移靠在沙发上,最近陈言做康复的时候他也跟着来了些器械,把自己折腾的全身疼,“其实我是真的很佩服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基因彩票,反正我看很多网友都说倒头就睡属于一种超能力。”
“他睡觉确实都挺不错的,”这个葛玥童承认,她是真的亲眼见过陈言说睡了躺下去就睡着了,入睡对他来说甚至比电脑开关机还要简单,“以前也挺能睡的,不到十点洗漱完了,六点起,中午固定睡两个小时左右,说睡就睡。”
“我刚开始以为他是装的,”虞移嘿嘿的笑着,“毕竟我是真没见过有人能睡的这么快,试了几次才发现学长他是真的睡着了,当然后来他嗜睡是因为缺氧哈,他嗜睡之前就已经够能睡的了,我其实特别想问问他都是怎么做到的,我感觉他要是能出本书或者搞个什么睡眠课,肯定是大受欢迎的,现在谁都缺这个好好睡觉,睡个好觉的能力。”
“学长,你最近睡的不好吗?”葛玥童总感觉虞移好像是在表达这个意思,于是就问了出来。
“当然睡不好了,”虞移转头看着葛玥童,“我一想到面试和试讲,我就慌得睡不着,然后又再想万一我就在迎大了,米新荷又不要我了,我可怎么办啊,总不能再灰溜溜的回京城吧,本来我爸就因为我决定就在迎大气的在家躺了两天了,我再干不出来点成绩,他们就更要让我回去了,我可不想和虞秩在一个城市里,也不想看我爸那张脸上那种让你不听话的表情。”
葛玥童和虞移相处的这段时间,她能感觉出来虞移骨子里还是个挺幼稚的人,甚至可以说眼前已经二十八的虞移还处于他的叛逆期里,之前心理辅导的时候葛玥童也看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心理学方面的入门图书,也知道虞移这样无非就还是希望他的父母能够看到,听到真正的他,但是他的父母显然并没有做到,所以虞移就一直处于这种漫长的叛逆期里,能够自我疏解自我抑制的时候就显得像个正常人,一旦移植到了临界值或者突然有什么事情触动,马上就会激烈的爆发一次,显得有点像个疯子。
难怪喜欢和陈言腻在一起,葛玥童心想,陈言善于察言观色,又是个体贴周到的操心人,他能够看到听到真正的虞移,并且给予他想要的反馈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