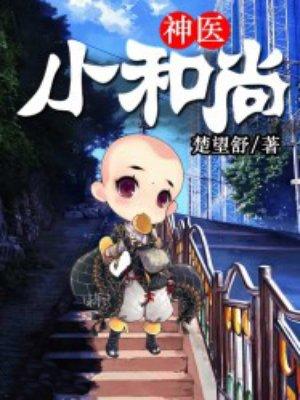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落花之女指什么 > 第一百二十九章大获全胜二(第1页)
第一百二十九章大获全胜二(第1页)
战绩展览会都是白天进行。到在晚上由解放军“六纵”文工团的演员们,在郭刚集西头,菜市场上,演革命文艺节目。四辆大卡车拼结成的一个大戏台,在左右两个大树上面,分别捆绑两个大喇叭,台下有解放军用手摇发电机操作,喇叭开始晌了,声音特别宏大,象似天外来客;第一场演出是革命歌剧《白毛女》,在怀远,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高水平的大型的歌剧。麦地里,大路上,都站满四乡八带的观众,还有道路两旁的大树上,也爬满了前来看戏的人。
演出开始时,台下鸦雀无声,农民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看戏。当戏演到杨白劳喝卤水时,台下开始出现了哭泣声。特别是喜儿哭爹时,台下也随之哭了起来。使当地百姓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憾,有的哭成泪人,有的妇女因悲痛过度竟然被搀扶出剧场。
就在这时,有一名解放军站在观众里,挥手一句一句地大喊道: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那名解放军喊一句,观众们便大声接一句,很激动,都是发自肺腑的,夜里虽说没有下雨,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流下眼泪,砸在地上,那呼喊声,撕心裂肺,俨如谁的声音小,怕自己变成第二个黄世仁似的。
演出结束,老百姓纷纷回到家中,向本村的老少爷们传达看解放军演出的消息。政府也要求解放军同志能继续上演《白毛女》,大家认为是解放军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使当地感受到了革命文艺的新天地。
清晨,金根姬和往常一样,扛着一把大扫帚和郭刚集上的妇女一起,在街上打扫卫生。不过今天她有所不同,用毛巾把脸围得严严实实——有些妇女干累了,干脆把棉袄脱了下来。
“金大姐,不热吗?看你用头巾把脸围得严严实实的。”
“俺不热,有什么可热的,天还是这么冷,再说一热一脱的容易生病的,我可不愿意生病。”
其实,她早想把围巾结下来,但是不能,为此她考虑了一天一夜。
怕在街上碰到过去的熟人,怕见到过去新四军淮北独立团的战士,怕见到章成生团长、桂平所长,还有的战斗中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如果见了面,谈起自己还没有回到朝鲜——那是多么尴尬的事情。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她在新四军队伍里是卫生员,是自愿退伍的老兵,还有什么资格同首长谈条件呢;在朝鲜的时候,自己是一个乡下人,可现在在中国,自己还是一个乡下人。
这样能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平安无事”比什么都好;没有必要向部队提什么要求,麻烦部队里的首长。
但人的遐思是无止境的,有时非常幼稚,有时又非常冒险,静静分析并深入探究自己内心的遐思,总是有千头万绪的奇妙境界。
后来她这样去想,种种不幸,种种贫因都过去了,现在怀远县解放了,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卖馍的,已经是大家的朋友了。
入夜时,也是金根姬最难过的时候,她没有到街上去听戏,可是大喇叭响起了,当听道,“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风卷那个雪花,在门那个外……”那种凄惨地歌曲响起时,几乎看到所有的听众都沉浸在白毛女感人情怀的悲剧中。金根姬坐在自家的灶前也听到了。她在案板上和面时,哭了起来;蒸馍时,一边拉风箱,扔是一边哭着。
金根姬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是通过与她在一起劳动的姐妹,才了解全剧主要故事情节,白毛女的遭遇与自己的遭遇,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天下的苦女人。白毛女的苦,人们知道,而自己的苦楚,有多少人知道呢?
金根姬自己知道,就是流再多的眼泪,也无法抹平这藏在内心的伤痛,但她仍是不停的哭——“说过了,不哭,怎么又哭了呢?没有出息。”她突然又自责起来。
再后来,部队文工团每次演出《白毛女》时,金根姬还是躲藏在屋内干活,不哭了,也不流泪。
金根姬的双眼顿时亮起来,那张脸也豁然开朗。她一直在馍房里转哟,灶火是红红的,在高温下,她那一张脸粉红似白的脸,象朵绽放的草花儿,包含着最强烈而又最温柔的情感。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