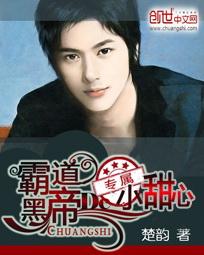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木乃伊英文 > 第143页(第1页)
第143页(第1页)
就在这半胁迫半镇压的方式下,斐特拉曼二世完成了他父亲的葬礼。有意思的是,在他将金字塔地门封上的那一刻起,那些曾经对他行为感到怒不可遏的人民似乎已经开始习惯了朝代的更换。他们不再抗争,也不再谩骂,仿佛那场七十天前在底比斯城墙外的杀戮,和底比斯被赫梯军队攻破所导致的沦陷,已离他们有一个世纪那么遥远,整座城市很快恢复了原先的运转秩序,亦适应了新的政权所带来的种种不适。与此同时,对于手到擒来的战果似乎完全不屑一顾的斐特拉曼二世,则很快开始了他对凯姆特另一座主城——孟菲斯的正式出兵宣战。“那真是个充满了野心的男人,不是么。”说到这里裴利安话锋一转,看向我道。“当他站在那张代表了一切王权的座位前的时候,你根本无法认出他就是当年那个备受屈辱、在生死的夹缝里勉强过活的奴隶般的孩子。我至今都还记得他跪在我面前看着我脚背时的样子,低垂着头,目不转睛,脸脏得几乎让人看不清他五官的样子。我让他舔我的脚背,他就舔了,没有一丝犹豫,像条乖乖听话的狗一样。而后来,当他指着地图上孟菲斯的方向说拿下它,紧跟着他就立刻去拿下了,像头雷厉风行的狮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底比斯沦陷后,你父王死了,你母后自杀了,而你却还活着的原因是么?”我道,“他进攻底比斯的时候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抵抗,裴利安,你这个凯姆特的王子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人了,因为你害怕那头狮子。”话出口的一瞬我有些后悔,我想这可能会激怒眼前这个男人。他是他故事里那个远得几乎虚无缥缈的男人,却又不是,因为现在的他和故事里的他似乎完全是两个人。“……我是说,其实这很明智,换了我也会那样做。”于是我吸了口气补充道。他看着我,眼神看不出有过愤怒亦或者别的什么情绪,只是那样静静地看着我,随后轻轻吸了口烟。“没错,这是我的艾伊塔才会说出的话,无论你承认与否,你就是我内心的另一个我。”“呵,你又……”“所以我俩才会同时被同一种人所吸引,那个可以像狗一样低贱,也可以像狮子一样伟岸的人。”“……你不恨他?”我微微有些疑惑。疑惑着他这话究竟有几分真假。却依旧读不出他的情绪,他低头看着指间绕动着的淡蓝色烟雾,笑笑道:“恨?为什么。我曾以为我是可以同他一起共同执掌那个国家的,靠着我和他之间互补的力量。”☆、110老斐特拉曼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底比斯大军一举攻破孟菲斯大门,将常年统治着那座城市、令老斐特拉曼每每想起就经常茶饭不思的将军菲姆迪斯的首级,悬挂在了孟菲斯最高防御塔的塔台上。取代他位置的是常年跟随在斐特拉曼身边的将军穆。裴利安说,穆是个很年轻也很沉默的男人。像个哑巴也像条最忠实的狗,在斐特拉曼身旁如影随形,说一不二。他为斐特拉曼屠杀了菲姆迪斯一万三千六百二十八名忠实的部下,被当地人恐惧地称作血之屠夫,而在他屠城后不久,斐特拉曼就在那座侍奉着太阳神拉的城市里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寺庙,叫安努寺,寺内供奉着死神阿努比斯,而裴利安的妻子艾伊塔,则被从底比斯的寺庙转进了这座新建神庙,成为它的最高大祭司。那是裴利安正式同艾伊塔分居两地的开始。他知道斐特拉曼为什么要把艾伊塔调去上埃及。并非因她对神的虔诚信仰,也并非为她对众祭司的领导力有如何出众。只因她是艾伊塔,尼罗河上盛开的夜百合,所以即便她是异族人,斐特拉曼仍能力排众议封她为大祭司;即便她已经身为王子的妃,斐特拉曼仍能堂而皇之地在公众面前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入底比斯太阳殿那扇金碧辉煌的大门。将他跟艾伊塔分开是迟早的事,送艾伊塔去上埃及能令斐特拉曼更为无所顾忌地同她在一起,关于这一点,裴利安自是心知肚明,且在众人非议的目光中沉默而隐忍着,正如当年年少的斐特拉曼是如何一天天在底比斯王宫的最底层,沉默而不动声色地忍受着一切,直至终于能从那座桎梏着他的囚笼中离开,并有朝一日回归,将囚笼变成了他手中所玩弄着的鸟笼。鸟笼。是的,对于裴利安来说,那些年的日日夜夜,他就仿佛是生活在一座巨大的鸟笼里,看着那个年轻而酷似自己父亲的男人君临天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甚至把他妻子据为己有。有人因此而唾弃他的软弱,但亦有人反而比过去更为忠诚地开始追随在他左右,因为他们觉得,相比斐特拉曼那令人恐惧的铁血统治,和对自己祖国民众生死的不屑一顾,裴利安才是真正适合统治这个国家的王者。他是如此仁慈,如此谦恭,不像斐特拉曼那样嗜好征战,也不会像他那样摧毁这古老国家历经千年的习俗和文明。况且他是老斐特拉曼唯一纯正王室血统的继承人,也是在斐特拉曼当权改变了全民宗教信仰之后,唯一一个敢默默坚持供奉拉神,且没有因此而被斐特拉曼怪罪的人。但他真的仁慈而谦逊么?那些死于他之手的奴隶和战俘们恐怕不会这样认为。每每在情绪有些失控的时候,他会退回到自己后宫最为隐秘的地方,在那里践踏着那些无力抗争的人,割下他们身上的器官,肆意玩弄他们,在他们尖叫和恐惧中发泄着日复一日被王座上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所压迫而出的愤怒。直到情绪恢复平稳,神情褪回仁慈,他才再次回到那片人来人往的世界,在斐特拉曼的身边静静伫立着,看他做着一切对或者错的决定,看他站在烈日灼灼的光线下完美得如同一尊真正的神祗。他知道总有一天那尊神祗会倒下,所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伴随着那个美丽女人的回归。因她亲口向他许诺过,带着她的卑微,她的忠诚,她所谓的爱,对他许诺,有朝一日她会为他将一切从那个神的手里取回来,只要她能在他身上得到她一直在寻找着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艾伊塔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他,每次他试图想对她知道得更多一些的时候,她就会慢慢解开她身上的衣服,一件又一件,直到露出她尼罗河水般柔软的胴体,再以尼罗河水般柔软而温婉的姿势跨坐到他身上,亲吻他瘦弱的身体上每一寸皮肤,直到他病弱的躯体开始有所反应,有所悸动,有所急于撕裂些什么、如同刀子般狠狠戳动些什么,并依此爆发的冲动。那种无论对周围那些卑微的仆从蹂躏过多少次,也无法令他真正感到满足起来的冲动。于是他便将一切都给忘记了,甚至忘记那令他痴迷的身体已在斐特拉曼的身躯下绽放过多少次,那令他疯狂的□声有多少次是因着那个神一样的男人而起……他忘记了,只任由那女人将自己压在身下,紧紧抓着他的双手,紧紧同他身体糅合在一起,再将他那勃发的欲望引进自己体内,然后喘息,发出那令神庙都会为之疯狂的声音,将他嘴唇咬住,将他舌头缠住,将他身下的灼热一遍遍撞进自己身体……说到这里时裴利安的面色有些不正常地潮红起来。他轻轻呼吸着,带着同他语调一样急促的速度,用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瞳孔看着我。随后在我试图朝后推开时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手指有力得令我不由自主尖叫了一声:“裴利安!”他瞳孔缩了缩。定定对着我脸上的氧气罩看了片刻,然后松开了我。“你这女表口子。”然后他冷冷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