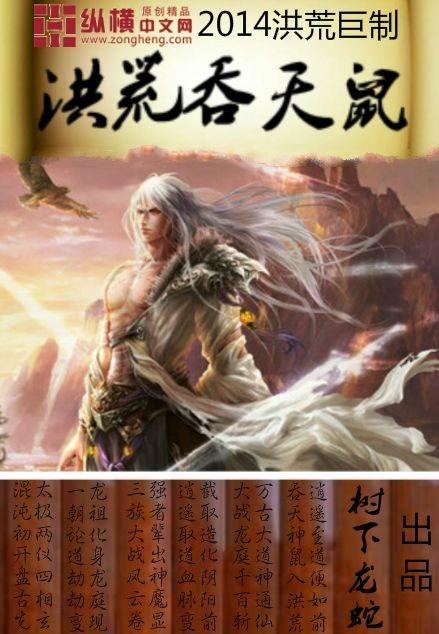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30日结婚作战计划 百度 > 117乖乖(第1页)
117乖乖(第1页)
容意这个人,漫不经心的时候京腔便不自觉脱口而出。
他眼神指了指桌上摆满的精致西点,柔声道:“今晚没怎么吃罢,陪我吃点儿?”
陈素冷哼一声,落座在他对面,淡声重复:“带回去。那些东西我一个都不会要。”
容意也当了回俗人,自那晚陈素从他那里离开,便天天差人送花送礼物。
他从没想过两人的关系会因此和解,存的是哪天她终于耐不住,愿意主动来自己面前的心思。
要给猫顺毛,不能在她不愿意的时候强行抚摸。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心肝儿尖牙利爪地重重咬你一口,再从挣脱你的怀抱跳开。
被挠伤的那点痛会好,可猫崽越跑越远要怎么抓回来?
容意的十指交迭,慵闲地搭在大腿上,看着她良久,才十分叹惜地回:“这么多天,你才终于忍不住要来见我吗?”
他的目光瞥了眼商厦门口来往进出的稀疏人影,又定定看回她,认真时的表情分外肃严冷峻,“可我天天看着你跟同事有说有笑,而一副对我无所谓的样子,人都快疯了。”
陈素嘲弄地一笑,把脸别过去,将注意清冷望向无意义的一处。
“你疯与不疯又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你。”
陈素自以为自己足够尖锐。可容意绝对有能力兵不血刃,用话就把人噎死。
她起身就走。
下一瞬,却被容意握住手腕。
拇指绵绵摩挲着陈素腕间的肌肤,那儿一圈淤紫红痕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可容意掌心指间的温烫,成了另一种印记烙印在手上。
容意眸里的淡雾一点点氲开,目光柔柔地觑她,“我知道,那很疼。”
陈素抵住下唇,不言不语。垂眸的一瞬,仿佛一块柠檬的酸涩从鼻腔发酵散开,连眼睛也齉住。
可她的眼泪保留着最后一点倔犟,没有掉下来,连吸鼻子的腔音都很淡。
那种痛其实熬一熬也能过去,可当有人小心翼翼、柔软地将其剥开,委屈反而庞大到无处可藏。
陈素暗自对自己说,争点气,他不过三言两语,你就这么容易心软吗?
那大约是容意平生唯一像哄孩童般,耐心对待一个人了。
他的手顺着那截脆弱的细腕往下滑,将不情不愿的陈素牢牢牵住,引到自己跟前来,然后屈起指节,心疼地替她揩去眼泪。
一边道,“好了,别哭了,乖乖。我知道错了。”
那点水泽,仿佛连他的心脏也泡软。
“我那样吃醋,怎么能不清楚你比我难受?”容意揉着她的手背,轻轻置于唇边克制地一吻,“我怎么就这么坏。”
他的难过与内疚都是真的。在让陈素痛这件事上。
可有时候,两个人谈感情就是这样。柔情蜜意时怎么都行,却容不得一点瑕疵。那是雪白纸张里的乌斑,是钉在眼睛里的刺。
陈素却躲过他落在脸颊的指尖,语气仍硬硬的。显然是不接受他的台阶。
“谁乐意听你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