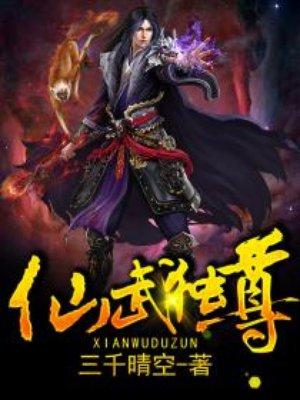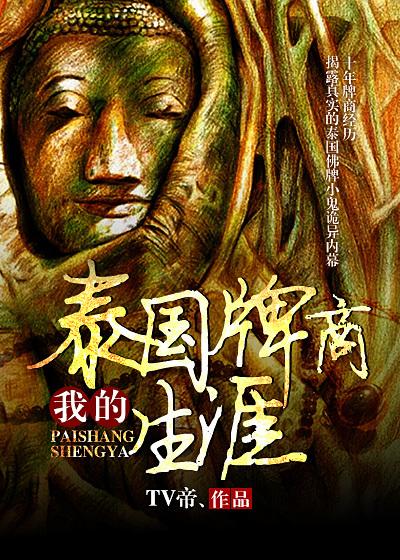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深池(黑道)作者梦为鱼 > 第73页(第1页)
第73页(第1页)
鱼俭捏他的脸颊,“多久没睡了?”
“没多久。”迟星咬着舌头软绵绵地说:“我都习惯了。”他笑了笑,带着极重的鼻音说:“我也没有那么贪睡,就是见了你才爱困。”
以前也是,他和鱼俭挤在一张床上时总要赖床。
鱼俭半抱着迟星伸手拦出租车,听见迟星的话伸手去挠他的胳肢窝:“这怎么能赖我。”
迟星躲着他笑了一额头的汗,已经是暮春时节,他身上还穿着一件厚的针织毛衣,鱼俭一只手圈着他防止他摔下去,一边撩开迟星汗湿的额发,问道:“谢菲尔德还冷着吗?”
“嗯……也还好,再说到处都是暖气,并没有冻着。”
出租车停下,鱼俭揽着迟星坐在后座,他一句话刚说一半就靠在鱼俭怀里睡着了。鱼俭定了一家宾馆,下车的时候看迟星睡得熟,先把他抱到房间安置好才去前台办手续。
迟星睡醒的时候已经是中午,鱼俭早上去商场给迟星买了一套衣服把他的厚毛衣换下来,他来得急,除了自己什么都没带。
下午两个人一起坐船回了老家。
鱼许两家的宅基地挨着,庄稼地自然也在一起,许外婆和许外公在东边,鱼奶奶在西边,隔着一条小路,想要叙话也方便。
“得,空着手来,”鱼俭一边拔着坟上的野草一边念叨,“清明除夕都不挨着,一时半会也没买到纸钱。奶奶,我先欠着,”他这满嘴跑火车的性子一点没变,还特意绕过一株野花没拔,“——这花给您留着别在头发上——等我下次回来一定多给您带些纸钱,就是不知道那边有没有通货膨胀,要不然还是买座别墅给你烧过去吧?固定资产折旧也慢些。”
迟星正在擦墓碑,闻言笑着说:“那你还要买两个纸人帮奶奶打扫别墅。”
“迟星说得对。”鱼俭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回头我多买几个。奶奶,我这么多年没回来,您别生我的气,生气的话也别气那么久,缺什么托梦告诉我一声——您要是暂时不想见我,让许奶奶和迟星说也行。”
迟星笑:“没你这么贿赂奶奶的。”
鱼俭其实带了两箱烟花,拔完青草便把烟花放了,催奶奶来看一眼。
白日里的烟花散开后不过几个亮点,鱼俭席地而坐靠着墓碑看炸开的光。
迟星去看外婆,也给鱼俭留一点私人空间同奶奶说话。
“奶奶,我,”鱼俭遥遥看着远处的迟星,含笑说:“我好好的,您别担心。”
“我以前有点怕回来见您。小时候我从树上摔下来,我还没哭呢,您抱着我先抹眼泪了,吓得我哭也不敢哭,一直说不疼。其实是疼的,那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们相依为命,我所遭遇的苦痛您也一分未少地替我尝着。您不在的那段时日,我不人不鬼地活着,只怕您看见了会难受。”
“后来,我快撑不住的时候,迟星回来了。”
“奶奶,这一生太长,自私容易爱自己难(注)。我努力了一下,发现爱自己实在太辛苦,就想着自私一回,等什么时候撑不住了,就在彻底变成鬼之前回来躺到您身边,我早就给自己留好了位置,打算不管您怎么嫌弃我,我都要赖在您这里。”
他年少时觉得天宽地长,无处不可去,又在折戟后像个怂蛋一样准备赖在奶奶怀里——生死都不让奶奶省心,是个不成器的孩子。
鱼俭揉着额头笑:“可是迟星一回来,我就不大想死了——您听见了肯定要说我是孩子脸说变就变——我那天闻到他手上的花香,就想起了小时候您给我搽脸的用的香膏,我一直嫌那种香膏甜得腻味,为了不让您生气,只好勉强凑上脸让您随便涂。奶奶,”鱼俭顿了顿,小声地笑着:“我喜欢他,也不想让他难过。”
“我想好好的同他过一辈子。”
迟星站在路边朝鱼俭招手:“鱼俭,快下雨了,我们回去吧。”
“就来——”鱼俭回一声,扶着墓碑站起来,“奶奶,我们下次再来看您和许奶奶,”他跳着往回走,一边喊着:“下次给您带别墅。”
回去的路上突然落雨,春雨绵软,砸在身上倒也不疼,只是衣服湿了小半。
“快走快走,”鱼俭拉着迟星跑:“今天赶不上最后一班船了,我们回去看看老房子还能不能住人。”
“鱼俭……你慢点。”迟星气喘吁吁地跟在他身后。
鱼俭边跑边笑:“现在知道健身房不顶用了吧,你这脆皮还是脆皮。”
迟星忽然笑道:“我多练练也跑不快怎么办。”
鱼俭回道:“那我只好投降了。”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笑起来,往事终于成了旧事,是可以拿来玩笑打趣的寻常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