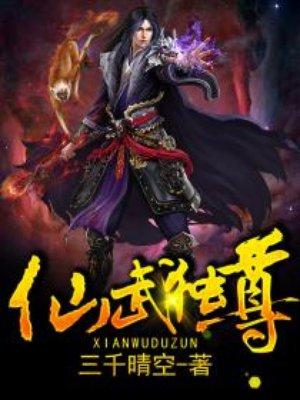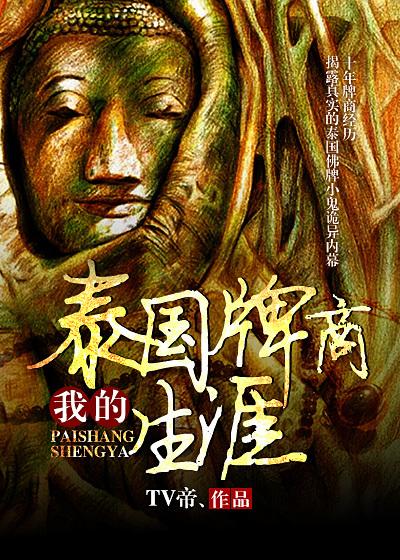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银行家访记录表内容怎么写 > 第43章 如隔三秋(第1页)
第43章 如隔三秋(第1页)
林霂离开超市回到医院的时候,季云翀已经睡下了。
她疲惫地坐在沙发上,身体往后一靠,臀部压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拿起来瞅了眼,竟是失而复得的手机。
林霂被自己丢三落四的坏毛病打击得无语了。点开屏幕瞧瞧,既无消息也无电话,遂把手机收到包包里,来到季云翀的床前,给他掖掖被角。
明天他就可以拆线了,改用长腿筒形石膏固定4周,固定期间可以扶拐行走。不过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周,股四头肌肌力萎缩,能够撂动右肢离开床铺吗?
要不先鼓励他多做抬腿练习,待恢复肌力,再让他慢慢适应新的走路方式?
林霂拿出纸笔列下季云翀的复健训练计划,修修改改,发现一个大问题——假期所剩不多,她即将回国上班,准备赴越援医资格的考试,没有办法在慕尼黑长期停留。季云翀一个人留在医院,能同意她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
林霂左思右想,想到个主意。
她忙碌了一整天,列完复健计划没有精力再做别的事,扯过毯子盖在身上,熄灭灯,缩在沙发上很快进入梦乡。
夜是静谧的,偶有几声春夏之交的蝉鸣。
病床上的季云翀睁开眼。
他转过脸,一双眸子沉郁浓黑,静静地注视着睡梦中的林霂。
夜色下,她面朝他侧躺着,呼吸清浅,满身月华。
这样的画面有点熟悉。那时她和他举行完订婚仪式,不胜酒力醉倒在他的怀里,满脸酡红,眼神迷离,见人就吃吃地笑。她被他抱回房间时,呢喃撒娇不肯脱衣服,却也不同意他离开,枕着他的手臂睡了一夜。
她真的很爱他,在梦里都喃喃地呼唤他的名字“翀翀,翀翀……”,不像现在连名带姓称呼他。
苦涩的滋味占据了整个心房,季云翀的嘴唇翕动两下,哑声道:“木木,乖啊,不要离开我。”
她没有回应,酣然入梦。
*
季云翀拆线后的恢复情况超出了林霂的预期。
他按照计划先做肌力恢复练习,三天后便可以抬起右腿,也能够下床拄拐走路。只不过他走路时步幅较小,身体呈10°向前倾,肢体活动不协调。
林霂安慰道:“你刚做完手术,缩短的右肢还没有适应强直状态下的膝关节,时间长了,步态会慢慢改观。”
季云翀信以为真,拄着拐艰难地在走廊里练习走路。
阳光透过窗户落进来,细细碎碎投照在他的脸庞。他的五官本就生的清隽好看,被温暖的光线晕染出一抹朦胧的柔光,眉眼间竟流露出几分纯真。
林霂的喉咙被酸酸涩涩的滋味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立在原地看着他步履蹒跚的样子。
普通人的一步,相当于他的三步。
仿佛感受到她出神的注视,季云翀侧目睨过来,挑唇一笑,笑容格外灿烂:“木木,我看起来帅不帅?”
她回过神:“帅。”
“励不励志?”
“励志。”
“招不招人喜欢?”
“喜欢……”她配合地回答,又突然噤声。
季云翀含笑的目光直勾勾地落在她的脸上,嘴唇柔软地上扬:“还好我没有放弃,终于等到你说喜欢我。”
他的语气是那么的满足,林霂不自在地清清嗓子:“哪有你这样说话下套的。”
她说话时垂着脑袋,错过了他眼睛里一抹转瞬即逝的黯淡,自顾自说:“今天天气不错,你想不想出去逛逛?”
这是她第一次邀约他。季云翀不假思索:“想。”
“我去找辆轮椅。”
春夏之交,日光暖而不晒,她推着他漫步在慕尼黑的街头。
街角的花贩们格外热情,缤纷妍丽的鲜花把这座城市从前段日子阴雨连绵的灰暗色调里解脱出来。季云翀见了,脸上的笑容也愈发明朗,问林霂有没有五欧元的零钱。
在这里,五欧元可以买下一大束娇艳的蝴蝶兰。季云翀抱着蓓蕾初开的花,挑挑拣拣拈下几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