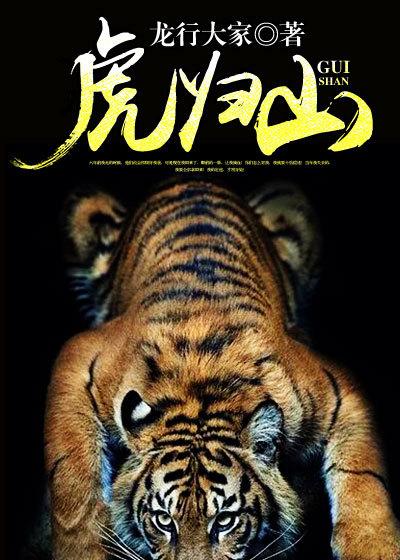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老公不咋的 > 第102页(第1页)
第102页(第1页)
“小友友,你真讨厌。”
“你多讨厌我,我就有多爱你。”
“讨厌啦。”
贾达友搂着一个染着金色头发的假洋妞,你侬我侬个没完没了。
周牧刚进来,就看到这腻歪歪的一幕,强烈抑制想吐的冲动。
“能不能控制一下你那大便脸。”贾达友抹着被亲在脸上的口红印。
“我给你面子,才没吐你一脸的隔夜饭。”周牧瞄了一眼,不知喷了多少香水的假洋妞,扭着腰枝去外面补妆。
“我这是调风弄月。”贾达友拽了句,新学的文词儿。
“少侮辱斯文了。”周牧抖掉一身的鸡皮疙瘩。
“二牧,说真的,你从大学毕业就没再找过女人?”贾达友对兄弟一头扎进票友堆里,大惑不解。
“谁向你成天爱来爱去的。不是每一种喜欢,都可以直接了当地说出口,还有一种喜欢,成了不能说的秘密。”周牧带着大青衣的端庄和哀怨,叹息着。
贾达友看他瞟过来的眼神,咋这么瘆人呢!让他浑身一激灵,缓缓坐起身,偷偷地坐到离他远一点的位置。“你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我事先声明,尽管本少爷帅得糊涂的,但只对女人有兴趣。”
“少恶心人。”周牧也表明自己比他还正常,又长长一声哀叹。“爱情啊!是勇气加运气的事。”
“就是矫情,哪有那么多真爱。说白了,男女之间不过就是,钱那王八蛋的事儿。”
贾达友精辟的结论,周牧并不认同,但他没有反驳。这是达友用过往,证明出的论断!他不好说什么。
王舒在考核新来的茶艺师烹茶技术,从温杯,醒茶,冲泡,她都看得仔细,不落下每个重要步骤的细节。
周牧躲在漆红的柱子后面,留意着她的一举一动,别人不注意的细节都流进他心底。她今天换了枚花朵胸针,和同款耳钉。柔顺的头发没有一丝毛躁,梳在脑后挽着。口红依旧是淡淡的,随便一涂就是那么好看。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青春期来的太晚,并且是鬼迷心窍的愣头青。正当他看得眼睛拔不出来时,手机铃声蹦出来,大为扫兴。“喂?”
“儿子,你跟王舒怎么样了?”周夫人期待着最新进展。
“妈...”周牧只在谈及到王舒,总是磕巴的让人着急。
“妈什么妈!人家可是有喜欢的人了,你还不近水楼台先得月。还要等到人家入洞房,你留着胆子去抢亲啊?”她这个儿子别看人高马大的,胆子比猫还小。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周牧不由得口是心非,外加拧巴地否认。“我...跟她只是朋友!”
他胡乱地嚷了一句,闪电般地挂断电话。冷不丁回头,王舒就站在他身后,瞬间心肌缺血,扶着粗大的柱子。“刚才是...我妈...她那个,不会骚扰...你。”
王舒看看了他,没说话,转头走了。
他心虚地不敢正眼看她,只有在她的背影时,才会投出爱恋的目光。
‘我们只是朋友。’这话听起来像极了不负责任的烂借口,成了他赖在她身边的游泳圈。只要隔窗相望,就可以继续假装相安无事,以朋友的名义,或上下属的关系,默默暗恋她。
王舒在洗手间的隔间里,就连上个厕所她都在想着工作。新来的茶艺师技术不熟练,看来要在招聘消息中注明,从事两年工作经验者,待遇优厚。
“这个月的薪水,我又被扣了三百块钱。真闹心!”员工甲抱怨着。
员工乙晦气地回,“三百算什么,我被扣了五百大毛呢。”
“怎么会这么多?你把汪汪狗给得罪了?”员工甲掏出口红,吃惊地问。
“迟到三次,捡了客人的戒指,被她瞧见了。”
“真牛啊,敢当着汪汪狗的面,私藏客人物品。”
“不愧为老板的狗,跟我抢了她家的东西似的。愣是让我拿了出来还给客人,不仅道歉还被罚了钱。”
“李姐,你好像比汪汪狗来得还早呢,怎么就让她成了老板面前的红人呢?”员工甲挑事儿地,问着后进来的人。
“会溜须拍马呗!像她那样的人,最善长的就是,踩着我们这种低头干活的人向上爬,才会被老板赏识。”李姐一向把王舒当成升职的障碍,视为眼中钉。
“是啊。”员工甲乙纷纷附和。
王舒冷笑,厕所里果然是滋生谣言,与不满的最佳场所。她被员工起了个响亮的外号——汪汪狗。顾名思义,在老板面前摇尾巴,对下属呲牙汪汪叫。
她从厕所里出来,身上带着一种高级感,来自于从容自信,甚至是亲切又自然,来面对恶语中伤她的员工。
“王助理!”两个员工像遇到灵异事件似的,其中一个张着抹了一半的口红嘴,能塞进一个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