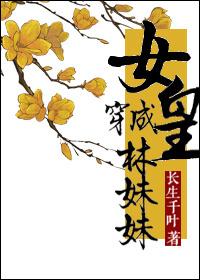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绿天庵图片 > 第12页(第1页)
第12页(第1页)
长生淡淡地看着陶祝,“兄长且去奔你的前程,祖父祖母的灵位尚且在此,我留下,替你守灵。”
“回长安一样可以守!”
“果真吗?”长生怀疑地盯着陶祝,“在,那种地方?”
“长生——”
长生面无表情地别过脸,“兄长好意我心领了。我一介山野村夫,不敢高攀替陶老爷办事。”
“不是替我父亲,是我,”陶祝顿了顿,“我要娶亲,会自立宅院。”
长生转过头,“娶亲?”
“当然不是现在,起码要等服完丧之后。而且,也还没有人选。”陶祝满怀期待地看着长生,“这件事父亲已经应允了,我回去即刻就能挑选宅院搬出来!你和我回长安,宅子交给你!一切都交给你!”
长生睫毛微微抖动,脸上的惊诧一闪而过,他默默笑起来,像是听到什么滑稽的事,逐渐笑得难以自持,“兄长,你这是做什么?让我给你当管家,明年好帮你迎娶娘子么?然后,再看你们日夜恩爱,将来再伺候你们的孩子?恭恭敬敬地叫他小郎君?哈!你替我安排的倒是圆满啊!”
“长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和你——”
“兄长!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如今是房州观察使,官位正隆,可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多少人嫉妒你、盼你登高跌重!”
“可是长生,我不愿你一个人留在这里。”陶祝说着,眼圈已经红极。
“我习惯了,兄长。”长生道,仿佛说着一件愉快的事,脸上的笑容格外粲然。
三天之后,陶祝动身回长安了。长生爬上山顶望着陶祝一行人渐行渐远,望了很久。第二天,他把锁着紫霜毫和香囊的木盒带去了绿天庵,埋在后院墙边的一颗古槐树下,连同自己五年来无尽的思念和等待一起埋葬。
☆、恨生
自从陶公去世,陶老爷就将山庄之人裁撤大半,只留下长生和几个平时看不上眼的老弱看管宅院。曾经盛极一时的陶氏山庄从此彻底寂静下来。
寥落无人的庭院让长生莫名生出几分厌弃,他于是整日在山林里游荡,与山中猎户混在一起喝酒打猎,快活度日。他以为他可以一直这样逍遥下去,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在山口遇见了一瘸一拐来找他的家丁老余。老余一见到他就嚎啕大哭,说陶老爷留下的那几个不要脸的东西想打祠堂祭器的主意,他发现之后一顿怒斥,可那几个混蛋竟然把他捆起来痛打一顿,然后将山庄洗劫一空逃之夭夭。
长生急忙奔回山庄,看见庭院里衰草连绵,仅剩的几个房间也被翻得乱七八糟,心中无比悔恨。他沉思几天,待老陶养好伤,和他一起把山庄整理了一遍,除去荒草,修剪树木,洒扫厅堂,他不知疲倦地打理所有的园子,想要维持山庄从前的模样,可无人居住的庄园还是一天天显出颓败之像。长生终于也厌倦了,他知道无论自己多么勤快,山庄还是会荒芜下去,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慢慢滑向生命的终点。
可他到底是不肯轻易放弃。他让老陶也搬进别院,住在自己旁边的屋子里,而另一边则是陶祝的房间。他每日起床都认真地洒扫庭院,把自己和陶祝的房间擦洗得一尘不染。山庄里没了供应,生活便全要靠他们自己。老陶在别院旁边的花园里开垦了一小块地,种些瓜果蔬菜,长生则去山上猎些野味拿到山下集市换成粮食和用品,倒也过得去。
然而山中岁月还是太过寂寥,长生无可发泄,只好把剩余的精力都用在了钻研书画上。毛笔用秃了几缸,没钱买纸,他便蘸着水在青砖上写,在墙壁上画,有时兴致起来,竟会两日两夜不眠不休。老陶时常觉得他要疯魔了,可当他回过神来,又变成从前的那个长生。
日子就在老陶算得上安闲的劳作中悄悄度过,直到三年后长生与陶祝再次相见。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长生正与老陶围着炉火聊天,山庄里突然来了两名军士,说是总督大人请长生到山下驿馆一叙。长生鄙夷地看了看两名军士,对老陶笑道:“他如今好大的官威啊,连自家的山庄都看不上了!既然要我下山拜见,我去便是。”
驿馆外集结着许多原地休息的士兵,长生看着他们疲惫不堪的模样,知道兄长这次只是路过。
两名军士把长生领进会客厅,恭恭敬敬地向陶祝复命后,迅速退了出去。
长生一路上的心潮澎湃,被映入眼帘的陶祝冷清的背影凝固了。
“你来了。”陶祝说着,慢慢转过身来。
长生看着陶祝清癯得近乎病态的脸,觉得自己的舌头像是被突然钉了钉子,发不出一个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