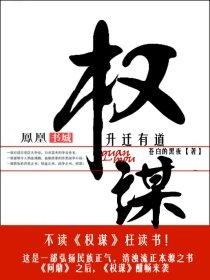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人鬼相通 > 第19页(第1页)
第19页(第1页)
本来可以一生都这样青春无敌,然而她对好友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介绍她与哥哥认识,促成了他们那一段悲剧的婚姻。她冒失地单纯地以为自己至爱的两个人能够彼此相爱,是一件世间最好的事情。然而她错了,她害了天池,令她失婚、绝望、自沉、失忆,即使醒来亦不能恢复元气与神采。堂堂“雪霓虹”的创始人纪天池,她的名字曾经响彻整个大连制版界,而今,竟沦落为给昔日的下属端茶倒水!琛儿几乎是有些失魂落魄地下楼,看着“雪霓虹”的金字招牌,竟然不晓得推门。对话声从门里隐约地传出来,是梁祝在责备小苏:“你怎么指使纪经理去给你买可乐?太过分了。”小苏不在意地说:“那又怎么样?她现在废人一个,除了端茶倒水跑跑腿儿还能干点什么?”琛儿再也忍不住,猛地推门进去,浑身发抖,指住小苏劈面就是一句:“你现在立刻给我走人!”小苏一愣,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还想再辩,梁祝早已将她一把拖到里间去,低声教训:“卢经理在气头儿上,你这会儿什么话也别说。走也好不走也好,补工资也好扣工资也好,都等改天心平气和了再回头来谈。现在吵起来,说什么她都是老板你都是打工,占不到好处去。”这边何好早已察言观色地端把椅子来请琛儿坐下,替她倒一杯茶,又将刚彩喷出来的校样郑重呈上,若无其事地笑着说:“这是车厂的设计初样,您看看能不能打动客户?”城门失火,难保不会殃及池鱼。天下打工的,都是息事宁人为上策,最要不得就是坐山观虎斗,惟恐天下不乱。梁祝与何好都是圆滑之人,这种四两拨千金的功夫玩得地道纯熟,当下兵分两路,里应外合地,将一场纷争在三言两语间遮掩过去。片时天池回来,屋子里各就各位,全然看不到方才剑拔弩张的硝烟气。她把复印件交给何好,又举着可乐找小苏,奇怪地问:“小苏呢?”“辞职了。”琛儿很平淡地说,仿佛在说一件非常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正是因为她这过分平静的口吻,反而让天池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因而猜测小苏的突然失踪并非辞职,而只能是辞退。那么,琛儿为什么会如此仓促地辞退小苏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自己,为了不让熟知过去的老臣子在自己背后指手划脚说东道西。这就像以前人家不得宠的姨太太喜欢换丫头一样,琛儿请了自己这个精神不健全的半个老板,明知不能压众,就只得靠辞退老员工来维持所谓的尊严。天池觉得深深的悲哀,自己是这样一个要别人处处迁就的弱者,一个惟恐打碎的瓶子吗?只是三言两语的闲话,已经让琛儿辞了共事多年的老臣子;天知道后面还有多少不可逆料的意外,要琛儿牺牲多少既得利益来成全自己?到这一刻,她才意识到程之方的话,她已经离开人群太久,强行要挤回到人群中去,逼得社会来适应自己,这不仅对自己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更对别人是一种难堪的负担。即使琛儿情愿担起这份责任,可是自己忍心让她锱重前行寸步千钧吗?天池整个下午没有再说一句话。到了晚上吃饭,却突然活泼起来,并且不住声地喊累,做出一副无赖的口吻对琛儿说:“上了两天班才知道,朝九晚五还真是需要几分功夫,我可不是那块料。明天拜托不要叫醒我,我习惯睡懒觉,再不想起早了。”“什么?”琛儿一愣,“你明天不去上班了?”“再也不去了。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永远都不想上班了,呆在家里多好呀,晒晒太阳看看电视就是一天,哪像上班,八小时对着电脑,红黄蓝黑的我根本弄不懂,真是自讨苦吃。”程之方笑:“这才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呢,前些天吵着要工作的是你,现在满口喊累的也是你。吃到苦头了吧?”琛儿却不以为然,知道天池决不会单单是怕吃苦这么简单。虽然现在的天池和以前那个坚强沉稳的形象颇有距离,可是一个人骨子里的心性是不会变的,天池决不是弱不禁风的娇小姐,她越来越怀疑程之方的专业水准了,还心理医生呢,连作秀和真心话都分不清。然而她也不想勉强天池,康复是一件慢慢来的事,何必操之过急。况且工作吃紧,她也实在顾不得猜测天池细密如针又复杂如网的心思。过了几天,一日琛儿偶然发现天池在翻报纸的应聘栏,越发认定了自己的想法:天池并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同自己一起工作,不想让自己为了照顾她而为难。这使琛儿觉得感慨也觉得欣慰,天池,毕竟还是以前的天池,那个善解人意忍辱负重的纪天池。她没有再去惊动她替她作主,却悄悄留意天池选了哪间公司应聘,暗地里打了电话通知对方手下留情。这天,天池很兴奋地回来,向大家宣布:我找到新工作了,是杂志社美编助理。堂堂电脑公司老板去做美工助理,亏她还这么兴奋。琛儿觉得心酸,天池是真的把她那些辉煌往事忘光了。她可还记得当年她是怎样在千百家设计公司与印刷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以一己之力取得大连服装节设计代理权的吗?那时的天池,何等潇洒出众,英姿勃勃!走错了时光隧道的天池,也许真是走不回来了。天池的工作,是卢越帮忙介绍的。自从在葵英路山墙下相遇,他们就开始交往起来。天池心中,隐隐只觉得对不起程之方,可是又不知道该怎样同他说,便索性将所有人都瞒住。琛儿、许峰、程之方、甚至核桃,一个也不告诉,找尽了借口溜出门去见卢越,见到了,便稚气地笑,散步,逛街,看电影,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喝一杯咖啡便分手,话也没有多说几句。只有十七八岁的少年才会那样盲目地约会。然而天池和卢越,又分明不是在谈恋爱。他们并没有任何暧昧的举止或是亲昵的话语,他们甚至很少说话,仿佛怕打破了某种约定。不可说,一说就破。茫茫中两个人分明都知道眼前的一切是不可靠,不久长的,却不由自主地要见面,多见一次,再多一次。想把快乐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又怕快乐落在了实处,打碎了。有一次他送她回家,经过广场时看到许多人在那里开露天舞会,两个人并没有商量,只是彼此对视一眼,便默契地加入了人群中,他拥着她舞在月光下,旋律中,她埋头在他的胸前,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心跳,那么铿锵有力。她忽然记得了——“我们以前跳过舞?”“很久以前。”“那是什么时候?”她抬起头,与他隔开一点距离:“为什么我一点都想不起?”“那就不要想。”他觉得害怕。怕那一点点距离,转眼就成天堑。他将她拉回到胸前,拥得更紧,“让我们从头开始。”然而她已经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从头开始?我们,从前是怎样的?”他竟然不敢回答。而她也没有再追问。他们仍然相拥着,但是距离却忽然远了。他觉得无力,他拉不回她,他和她之间,的确有个天堑,不,是恨海,他不是精卫,他填不平它。只有真相才会让她消除隔阂,然而真相会使他们彻底疏离。除了听天由命,他毫无办法。天池说要找工作,卢越立即介绍相熟杂志社给她,虽然只是美编助理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然而天池已经很感激,特地请他吃饭道谢。席间,卢越终于难得地提到过去:“以前你离开制版公司要开‘雪霓虹’,也是我帮你转工。”“是吗?”天池苦苦回想,“我依稀记得在一家中美合的制版公司做过一段时间业务经理,后来辞职出来,开了‘雪霓虹’,但是具体情形却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