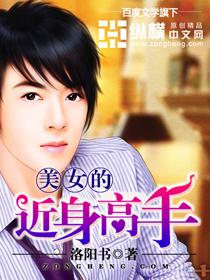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红楼华彩免费阅读 > 第201章 不服去告(第2页)
第201章 不服去告(第2页)
巷口马车里,一碗甜汤摆在小桌上,调羹略略搅动,李惟俭盛起一汤匙略略尝了尝,随即怅然若失。
这鸡头米做的甜汤,果然还是七、八月吃最合适。过了季留存下来的鸡头米,实在不新鲜。可好歹还能吃个味道。
此时天已过午,早就过了约定的时辰,吴海宁等得百无聊赖,这会子跑去墙角数蚂蚁去了,李惟俭却半点催促的意思也没有。
母女重逢,若短促相会便分别,那定然是谈崩了。这会子还不曾出来,料想此番能解了晴雯的心结吧?
临近未时,柴门打开,晴雯依依不舍地从小院儿中行出来。那妇人不住地啜泣,晴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嘱咐着什么。过得好半晌,那妇人倚门而望,看着晴雯一步三回头地上了马车。
“四爷……”
看着晴雯眼睛好似一双烂桃,李惟俭叹息一声,说道:“怎么不多待一会子?”
晴雯只哭着摇头:“总归是要走的,迟一些、早一些又有什么区别?”
李惟俭思忖道:“若你舍不得,不若回头儿我打发人带了你父母一道儿去京师,左右老爷我家大业大的,也不差安置两个人。”
晴雯摇头道:“娘身子不好,去了京师只怕熬不住冷。”
李惟俭便不再劝说,扯了晴雯的手抚着。马车辚辚,晴雯隔窗回首看着那柴门前的身形,泪珠子又止不住地往下掉。
出门前娘亲嘱咐过莫要声张,免得被邻人知晓了,再转告其父。晴雯便一直忍着,直到眼看出得巷子,晴雯终究忍不住喊了一声:“娘”
妇人死死捂着嘴,张口翕动,晴雯虽不曾听见回应,却也知娘亲也在喊着‘鹊儿’。
骨肉生离,最是让人动容。待马车行远了,李惟俭这才揽过晴雯,不住地安抚,只道来日得空再来瞧其母亲。
晴雯又哭了好一会子,直到马车出了苏州城,她这才低声道:“四爷,娘亲不曾忘了我呢。”
“嗯。”
“吸娘亲还攒了银子要赎我呢。”
“嗯。”
几年的郁结一朝得解,晴雯宣泄似的哭过,只觉心下无比畅快。她死死箍住李惟俭,过了好半晌才道:“四爷,过几年我真能回来瞧瞧我娘吗?”
“呵,我何曾骗过你?”
晴雯便破涕为笑,额头不住地在李惟俭的胸前蹭着。
一路到得蟠香寺,此时天已近黄昏。马车停下,二人自其上落下,李惟俭随意一瞥,便瞥见一抹红裳朝着那湖边行去。
这些时日忙忙碌碌,便是撞见了邢岫烟,也不过是说过两句话便匆匆别过。想着明日便要启程,李惟俭心下一动,冲着晴雯说道:“你先回去,我下去转转。”
换做往日,只怕晴雯还要追问一番。可此时晴雯满心都想着娘亲,一时间竟忘了追问,只嘱咐李惟俭快些回来。
李惟俭应承了,旋即带着两名禁军朝着湖边行去。
日垂西山,晚霞成绮,李惟俭信步走在湖堤边,身后远远缀着两名禁军。许是方才瞧错了,李惟俭找寻了半晌也不见邢岫烟的身影。
他便自失一笑,只道怕是没机会道别了,继而干脆停在湖堤边眺望南面的西山岛。
岛上每日产出的水泥,通过舟船尽数运到苏州、昆山,如今知府庄有恭正发动百姓修筑石塘,料想六月里梅雨,今年总能好过一些。起码昆山不至于六成土地尽数成了泽国。
此番不等股子交易所开张,那四成的股子便尽数发卖出去,便算是结交江南士绅了。这回顶多算是混个面熟,因着时间实在太紧,只能留待下回再与这些士绅交往。
不过嘛,他与这些士绅全然是以利相合,便是不用刻意结交,这班人也迟早得上他李惟俭的贼船。那些织场的东主纷纷打发人入京求购锅驼机,待蒸汽机在江南遍地开花,此地自然就成了李惟俭的拥趸、基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