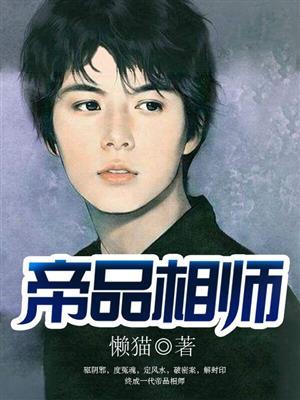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香江风月在哪里看 > 第134章(第1页)
第134章(第1页)
他额上两条交错的青筋似雨中河流,一瞬之间暴涨起来,下一秒就要爆裂释放。
燕妮已然做好承受暴风雨的准备,但她等了又等,最终只等来一声细不可闻叹息。
“时间不早,去吃饭吧。”他最终妥协,低头将几乎被被碾碎的戒盒收进口袋,选择用成年人的方式体面而周全地结束这一场由上帝见证的失败求婚。
燕妮望住他佝偻下弯的背脊,胸中不由得响起哀鸣。
她一面心疼他,一面又能狠下心拒之千里。女人真是矛盾,不可能成全自己,亦不肯成全他人。
她在命运的惯性当中挣扎,停不下来。
“好像还在下雨。”陆震坤孤身走在前面,呢喃低语,仿佛说给自己听。
燕妮慢慢赶上来,他推开门,两人便站在教堂大门前,如同两具失去灵魂的肉身,迷茫地漂浮在匆匆忙忙人世间。
“雨停了。”她的声音同样细如蚊蚋。
过后谁都不愿再开口,他与她肩并肩,站在门前看夜。
只是黑的夜,连星光都透不开它浓稠厚重的底色,月的影、灯的影都只是被蒙在黑幕下的斑驳。整个城市窥测不见鲜活气息,浑然已成为一座地狱死城。
到最后无人再记起那一间属于上流人士的法国餐厅,他与她在沉默中回到榕树湾别墅,燕妮甚至对回程的记忆都一片空白。
恍惚之间,他听见陆震坤说:“我在楼下抽根烟,你早点休息。”
“嗯。”她下意识地应承他,转过身,慢慢上楼,慢慢消化今晚发生的一切事。
等她洗完澡,头发吹到半干,走出浴室时,床头灯竟然亮着,床上坐一位失魂落魄英俊男士,他的性吸引力因他的精神孱弱而几何增长。
就连燕妮都要被激发出母性光辉,忍不住想要上前拥抱他,告诉他没关系,不要紧,天涯何处无芳草,全港不知多少女人等你求婚,何必在乎她一个?
下一秒便咬住下唇,用疼痛提醒自己,不要精神错乱,一不小心讲错一个字,令自己今生今世都活在后悔里。
她擦着头发,慢慢走向床边,“你…………”
话还未能说出口,便被床上的男人一把抱住,双臂环她腰身,侧脸紧贴在她胸前,在冰冷世界里寻找安慰。
“一定要走吗?”他将头埋在她胸前,闻着她皮肤上香草沐浴露绵延的余味,闷着声,不甘心地问。
燕妮照旧回答:“我有我的人生。”
“我不会让你走。”他抬起头,目光决绝,言辞激烈,“你以为你能走得了?我宁可杀了你,也不会让你离开!”
生与死的威胁,竟然只能换来燕妮淡淡一笑。
此刻她看他,更像是看一个得不到中意玩具的顽劣男童,失望过后无理取闹,损招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