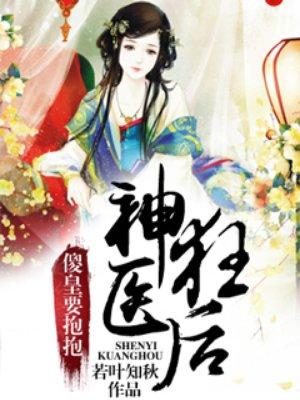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郁金堂青衣呀 > 第169页(第1页)
第169页(第1页)
武延秀哎呀了声,恍然扶额。“臣竟疏忽了,相王之子李隆基在羽林做尚辇奉御,掌管内外马匹,职位虽低,又不掌兵,到底在要紧郎将手底办差,熟人熟面儿,最易下绊子,添闲话。”凝眉等他示下。“羽林动不得,那……?”李重润不说话了,沉默良久,调转视线望向他。他脸型极硬朗,眉骨如弓,下颌似刀,毫无女气,唯一双眼深邃秀美。新换的衣裳素绢絮棉,青白两色,暖和寡素,犹如丧服,二姐用心良苦。相王与太平是阿耶的嫡亲手足,但多年隔绝,至亲至爱一旦生隙,反不如外人来的踏实可靠,譬如武家两府,便是东宫一条绳上的蚂蚱。和声提点他。“春官发的国书,写明你六月出发,八月抵达,是为夏季道上草长莺飞,车队好走,照我想,不如提前些,冬日就走……”武延秀纳闷,“早走?那我阿耶?”“二月初出神都,走潞州、太原,冬天艰难,估摸到太原已是上巳节,再往北,走灵武,至多到安北都护府,定有一段大雪封路,那时就说嫁妆车子翻了,他们要的丝绸、草药全没了,朝廷另外预备,你便留在原地。”“那就是骗默啜?”武延秀嗳了声,发觉这太孙真不一般,“两国相交,何来欺骗?”李重润望着漫天静静落下的雪,缓声道。“不喊打喊杀便是至交密友,默啜好战,继位十年,四面开战十七八次,劳师动众,耗费人口,想来部众多有不满,咱们搪塞一两个月,他派谁来催问,便盯上谁,还能套些话来。”青阳显是他得用的人,接上来道。“使节传信回去,说默啜另派人马迎接郡王,人来的越多么,越好办事。”一面说,接过侍女呈上来的羽扇,小心翼翼料理李重润脚下的炭盆。上用的西凉炭,长达尺余,铁棒样,靓青色,瞧来瞧去总没有火焰,却热力惊人,烘得武延秀手心里汗津津的。“东宫卫已在筹建中……”渺渺看他一眼,不等他装模作样质疑,直接道。“相王只是右卫率,这些私事,我托给左卫率办就是了,估摸月末能成。五月之前,我给你准信儿!”武延秀大喜过望,忙向李重润揖手行礼。“多谢太孙,请太孙放心,臣此去定然多方刺探,摸清突厥底细!”太漂亮的人缺乏年龄感。武延秀的侧颜青涩,下巴上胡渣故意不刮,好显得沉稳些,他困在西宫时也有过这般做作,如今增长自信,反而不必了。“圣人择你去和亲,未必有这个想头,可我不同,不愿养虎为患,放任默啜坐大,往后年找一回麻烦。为人主,当居安思危,如今国朝铁骑三十余万,自能威吓四方,往后呢?”李重润抚着腕子上十八子的菩提串儿,深深望他一眼。“若能以一战解百战,自是最好。”武延秀大感意外。国朝事务万千,不说凤阁、鸾台,单文昌台,一日大事少说七八件,小事又有二三十件,但其中,唯有外交军政最大最要紧,尤其改变女皇既有决策,决除突厥,那不单是僭越而已,甚至有提前继位的嫌疑。——他打了个哆嗦,李家当真有此野心,又何必透露给他知道?“臣,不明白……”李重润笑得坦然,毫无乱臣贼子罗织阴谋的鬼祟,笑着指指他身侧。骊珠大有不留下武延秀决不罢休的架势,扳着阿大的脖子呜呜哝哝抱怨,两条短短的小胖腿使劲踢腾,把那深红的地衣都蹭卷了。琴熏不肯惯她的坏脾气,只做看不见。唯有莹娘握着她手,一遍遍道,“国朝威武,总有一天能解决突厥之乱,那时六哥就能回来!”骊珠不信,“那是什么时候?三哥说可汗刚四十岁,且折腾!”“六哥也不过弱冠啊,怕他?自古英雄出少年。”粉雕玉琢的雪娃娃,五官还没长开,口齿粘缠,尤其才哭过,还带着隐隐的鼻音,多么软糯招人疼,合该富贵乡里无聊消磨,却认认真真说什么突厥。武延秀听得发笑,也感激杨家姑娘毫无保留的信任。看李重润一眼,见他亦是满眼快意,扬声插口。“表妹高看我了,我是去和亲,又不是去打仗。”莹娘定定神,侧头朝他微笑。“两国彼此提防,和亲也如打仗。”雪越下越大,团团簇簇,打在霞影纱上,沙沙的响,像春蚕吃桑叶。莹娘怕冷,穿了件织金官绿纻丝袄,上罩着浅红比甲,衣裳裁得恰好,她又拧着腰身,愈见纤细婉转,窈窕好女。武延秀没想到这小小女娘瞧着跟瑟瑟差不多岁数,竟颇有见地。他很欣赏,转念一想又觉遗憾,带着几分对未来的茫然,淡淡答她。“两汉以来,和亲的公主尽多,有三两年就香消玉殒的,亦有四十年艰难维持的,此去前路如何,我实在不知……”提杯在手,以茶代酒,潇洒地一仰脖。“可是表妹的好意,我心领!”莹娘很震动。美人在骨不在皮,武延秀的清艳激烈,单在纤纤十指间已是一览无余,骨节匀称修长,如翠竹拔节,衬着拇指上赤金游龙嵌宝的扳指华光璀璨。“我,我不是空口说些好话。”莹娘小心翼翼又很认真地望着他。“我不是哄小县主,我是……我真的相信六哥能回来!”武延秀想了想,又觉得没什么值得细想,简单道。“那就借表妹吉言。”莹娘说出口便松快,并无其他索求,大方地朝他一笑,起身叫骊珠。“我带你洗个脸,待会儿吃饭了,瞧你哭成个大花猫。”李重润含笑目送,收回目光乜了武延秀一眼。“九州天下,人同此心,皆盼望太平盛世,连莹娘、骊珠小小年纪,也懂得靠和亲解决不了问题。”武延秀凛然。“太孙的意思是……?”李重润挑他一眼,嫌他太过谨慎。“三郎说你胆子很大,六岁便敢忤逆魏王,打二十板子,一天不给吃,梗着口气绝不低头,如今果然又是你,敢抻头怀疑圣人。”提起武崇训,武延秀的拧劲儿上来了,皱眉道。“您要打听臣的为人,何必绕远道儿?他那般四平八稳,贪生怕死的人,能有什么见解?哼,真真儿是问道于盲。”武崇训约束他,反而犯他忌讳,蹦跶得像头野驴。李重润伸出两指撑住太阳穴,慢慢道。“你是这个脾性,我还真不信你为了个郡王衔儿,就肯自缚手脚,乖乖去给人当上门女婿。”武延秀沉默了下,转头望舱里姓武的一大家子人。武延基两口子挨着琴娘,正在说瑟瑟得了驸马便忘了旁人,着实可恨,他心里牵牵的痛。那种爱而不得流露在脸上,正是去国离乡之苦。他没在作假,实是真话,合眼道,“全在这里,我能如何?”所以到底还是以亲情为重,哪怕骨肉至亲苛待他多年,临到这时候,反而怕自己肆意妄为拖累了旁人……李重润感同身受,他的千般算计,亦全是为了爷娘姐妹,为阖家团圆。才坐下时陪李真真喝了两杯,这时酒劲儿上来,人便容易伤感,尤其这炭盆子太热,烤得他困意连连。“你此番去,下策自保,中策么,便是取得默啜信任,缔结友好之邦。”他笑了声,指尖在圈椅上摩挲,居高临下道。“但若论上策……”武延秀眉峰一跳,从中揣摩出了惊人的计划。“您是说,要我趁着这样刚猛好战的可汗坐镇,寻条缝子,巧加拨弄,好比郭元振在野狐河那般施为,一举拔了西北这颗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