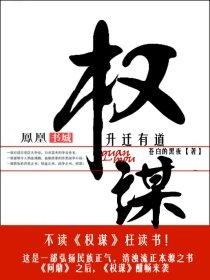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六宫粉黛无颜色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 第423章(第1页)
第423章(第1页)
定柔将脸埋进那个胸膛,握拳打在肩头,话不成声:“我就是受不了哪怕只是怜惜,我也受不了你心里有别人半分!你即喜欢她,为何不喜欢到底,为何来招惹我啊,慕容定柔一旦许了,就是全心全意!”
皇帝任由她一拳拳落下,双臂越收越紧,掌心握着发髻的后脑,只恨不得将她融入自身。
良久之后,语气冷静了下来:“我也受不了你心里有别人半分,哪怕只是怀念,我也不许。”
她的整张脸抵着胸肋,泪水浸湿袍角,终于抽光了力一般,双臂一收环住了男人的腰身。
不知相拥了多久才松开,他指拭去她眼角的泪痕,一张小脸低低垂着,固执地不肯抬头。
他轻轻吻着眉心,柔声说:“我真的早就将她放下了,从淮南回来就放下了,我与她就如你姐姐对我,当初不过眷恋那一瞬的感觉,那情那景,我就是明白了她不是我寻的那个人,才放下的,与她只是皇帝和嫔妃,她是什么性子我清楚的很,她心里想什么我也真知灼见,她怎能与你比呢,你是赵禝明媒正娶的娘子啊。”
定柔低垂着眼睑,眉心舒展开来,心口仍揪扯着疼:“我曾经也选错了,被自己的错觉给误了,从嫁给你那一刻就放下了,真的放下了。夫君,你其实很在意那个对不对?你气我当初没有选择你,对不对?你一直在克制自己对不对?逼着自己做一个完美的夫君。”
皇帝摸着她发上的玉簪,伤感道:“莫道不惋惜,只恨自己不曾在最好的年华娶到你,但是这些比起我们相守一生来说,算的了什么?我在你眼中是个浅薄狭隘、反复无常的小人吗?我对可儿是真心的,我真心希望用自己的权利呵护她一生,如有半分虚伪,叫我短折而死!”
她伸手堵在了他的唇上,泪水再次泛滥,使劲点头:“我以后不会这样心胸狭窄了,你虽是我的夫君,可对她们同样也有一份责任,守护她们的安危,我懂了。”
皇帝再次将她箍入臂弯。“好娘子,我绝不会伤你的心了,以后只要你不喜欢的事,我绝不做。”
此后第二日,太后领着妃御们到御苑赏牡丹,嫣红落粉如富丽多彩的锦缎。
花卉局呈出一百多个汝窑镂空吉祥盆,其中有新培育出来的珍品十余种,一株名曰“玉楼春”在百紫千红堆簇中分外清丽,因失败多次,只育出了一盆,莹白如雪的花冠,层层积叠似玲珑小塔,花姿圣洁无暇。定柔很是喜欢。
太后转到游廊尽头的闲云亭小歇品茶,隔着假山,皇后和众妃时时跟随着,走远了,定柔对月笙使个眼色,快将这一盆搬回春和殿。
正这时,一袭提花杏缎风袖大衫的女子和从旁边花丛转过来,绾着随云髻,娟好静秀的面容,神态楚楚,眉角带着病后的荏弱慵态,身后跟着两个宫女,对定柔敛衽福一福,请了个金安,然后说:“纯涵方才对太后说了,这株赏给嫔妾的思华殿。”
定柔转眸看了看,不就一株花草吗,曳着裙裾往闲云亭去,刚走了两步,身后的声音问:“娘娘,您的春和殿有水晶帘吗?”
定柔脚下顿住,诧异地回过身,林顺仪端的姿态娉婷,嘴角轻轻扬起,这样一个清纯佳人,笑起来面目无害。定柔已察觉到了挑衅,于是答道:“就那个云母晶珠吗?我母家的山月小筑偏厅有,总是叮叮咚咚响,本宫喜静,是以不喜欢。”
林顺仪笑如花绽:“可纯涵很喜欢呢,小时候嫡母的房中有一扇圆月格栅门,直通后头小花园,就挂着水晶帘,会折射像彩虹一样的光,纯涵每回去了都忍不住多看几眼,总想碰一碰,可嫡母凶,纯涵不敢,纯涵那时便幻想着,将来有了自己的房子,将它也辟出一个圆月门,装点的典雅精致,全都挂上晶帘,连门窗也挂满了,我坐在里头看七彩流华。”
定柔不得不逼着自己听下去。
林顺仪满目憧憬:“那年梨花树下初相识,陛下说,他要守护纯涵,守护这一晌春景。
入宫后,他对我百般体贴,但凡纯涵想要的,一个眼神便心意相通。他知纯涵所喜,便将昕薇馆劈出一扇圆月门,挂上晶帘,他知纯涵喜弹箜篌,便费尽心思寻了一架凤首箜篌。后来到了思华殿,陛下命工部按着我的喜好装饰,帘幕全部换成了晶帘,后殿打通一个小花园,雕花格栅门,植缸莲,建花圃,四季供着锦花绣草。只有思华殿有,娘娘,这些陛下可也曾如此待您。”
定柔掌心攥出了冰冷,鼻端阵阵酸涩,但当着这个人,她不想失了风度,站直了身子,唇畔展开灿漫的笑:“陛下与本宫心心相印,他对我的好不是用来与人攀比的,我作甚要告诉你?”
林顺仪继续道:“那一夜,他抱了我一整夜,喂我服药,安慰我,一直到我入眠才放心。”
定柔丝毫未见愠怒,依旧笑着:“顺仪是想对本宫倾诉与我夫君’曾经’的浓情蜜意吗?本宫正无聊的很,不如我们找个凉亭,你慢慢说,叫他们拿茶来咱们喝着,本宫洗耳恭听。”
林顺仪不想她会如此说,怔了一瞬,也狠咬银牙,道:“娘娘何以敢僭越称陛下为夫君?如此摆不正自己的位子,我们是妾妃,连皇后娘娘都是臣妾,你竟骄宠至此。”
定柔听着这话,心中霎时底气十足,更加无所畏惧起来,索性向前一步,眼角带着凛然的光,气势迫人:“本宫称陛下为夫君,也缘自他唤我娘子而起,敢问顺仪,他可曾唤过你一声,娘子?可曾对你说过,要执子之手,相携白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