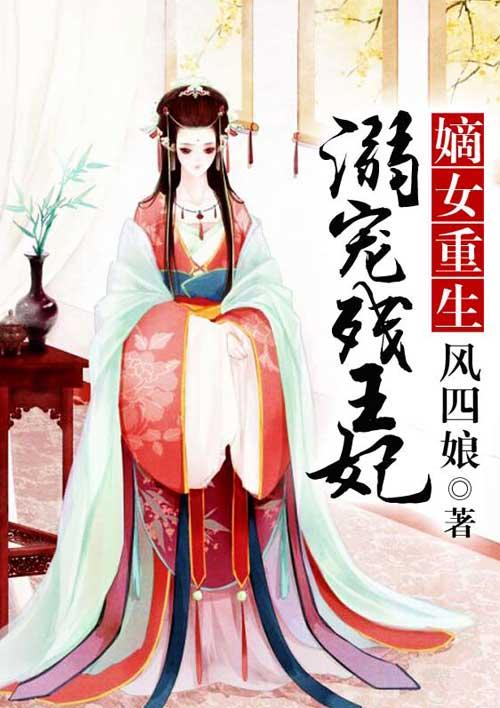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特务迷城国语完整免费 > 第22章(第1页)
第22章(第1页)
于守业无路可退了,他睁大眼睛,盯着韩同志手里的信,天旋地转,分不清南北了。那是哥哥寄给陆城台办的一封寻亲信,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对于守业的情况也讲得一清二楚。哥哥在信上说,1948年时弟弟就在陆城当老师。哥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并没有说明他留在大陆的真实身分。信里还夹了几张哥嫂一家的照片,看着照片上的亲人,一条时间的河流仿佛在眼前穿过。他摩娑着手里的照片,浑身颤抖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三十多年前那个雨夜,他站在街边目送着哥嫂一家离去,便再也不曾相见,只在电波里听到过哥哥惟一的一次呼唤。从此,关于哥哥的信息被他深埋在了心里。只有在夜深人静,突然从梦中醒来时,才会想起哥哥一家,然后就是长久的空落,无边无际。他原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哥哥了,兄弟天各一方,只剩下无尽的思念。没想到,哥哥的消息竟奇迹般地浮出了水面。
韩同志看了照片,又看了他,长舒了一口气。不用他承认,韩同志也能确信他就是哥哥要找的人。韩同志兴奋异常地告辞了,走时还拉着他的手说:你哥的地址已经知道了,以后你们就单独联系吧,请他回来看看,大陆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啊。
接下来,退休的于守业就繁忙起来。陆城的台办经常组织台属搞一些活动,讲国内的形势,宣传政策,希望台属们把大陆的亲情传达给海峡那一边的亲人。
李大脚早就从东方红副食店退休了,昔日的东方红副食店已经改成了一家超市,仍然红红火火地经营着。李大脚做梦也没有想到,老实巴交的于守业还有海外关系。改革开放初期,谁家要是有海外关系,那是比别人要高出一头的。风水轮流转,现在不比从前了。她望着于守业,&ldo;咦&rdo;了一声,又&ldo;咦&rdo;了一声,然后就拍着大腿说:老于,你行啊。俺跟你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听你说过,你还有个哥哥在台湾,看来俺这么多年没白跟了你。
于守业就苦笑着,摇摇头说:那会儿我要说有个哥哥在台湾,你还敢嫁给我?
于守业哥哥的出现,让李大脚比于守业还要兴奋。她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树下,畅想着说:老于啊,啥时候你带上我,咱们也坐回飞机去台湾看一看,让俺也开开眼。
于守业就笑,他和李大脚一样,心里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他现在不停地和哥哥保持通信,他在哥哥的信中得知,五十年代末哥哥就离开了军队,拿了一笔转业费做起了小买卖,后来又办起了工厂。现在是一家电子元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就是于陆生。哥哥还说想家,想回大陆来看看。他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哥哥,当写到小莲时,他的心又疼了一下,眼泪在眼圈里含着。回头再去看李大脚,见她正热切地望着他时,他把眼泪咽了回去,客观地写了自己的情况。他情真意切地在信里说,这么多年,亏了老婆桂芬的照顾才平安地生活到现在,她是自己的贵人。也许他的这句话,只有他和哥哥才明白其中的潜台词。
哥哥在信中喟叹人老了,总是想老家,想亲人,叶落还知道归根呐,何况人乎。
他看了哥哥的信,就唏嘘了一阵,又一阵。一旁的李大脚听于守业读了哥哥的信,没心没肺地说:你哥想回来,那还不容易!买张机票飞回来就是了。
终于,哥哥在信中告诉他,自己想好了,无论如何要在最近回来一趟。
于守大要回来的消息,风一样地在胡同里传开了。老邻居们不停地过来打听消息,样子比于守业一家人显得还要急迫。
于定山已经和于守业来往了,昔日梗着脖子的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原谅了自己的出身,正视了现实。清明节的时候,他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声泪俱下地哭了一场,媛媛一旁也抹着眼泪。于守业背过身去,强忍着眼泪,哽着声音说:儿子,你母亲终于能闭上眼了。
于定山和媛媛也是做父母的人了,他们的孩子于展望已经三岁了。做了父母的于定山和马媛媛,看开了很多事,也解开了许多的疙瘩,于是给孩子起了名字叫展望。
14叶落归根
哥哥于守大终于辗转着回到了陆城。不仅哥哥回来了,还有嫂子和陆生。亲人再次相见了,见面的那一刻,兄弟俩呆呆地对视着,他们从对方的身上看到了岁月的痕迹。几乎是同时,他们想起了四八年陆城分别的那个雨夜‐‐哥哥是中校科长,才三十出头,弟是中尉参谋,二十六七岁的样子,风华正茂,此时他们的头发花杂了,眼睛也浑浊了。他们相望着,还是哥哥先伸出了手,痛楚地叫了声:守业啊,三十多年了。兄弟俩就拥抱在一起,老泪纵横。积攒了三十多年的话,东一句、西一句地拼凑在一起,勾出了历史的轮廓。
一家人终于相见了。李大脚和嫂子也搂抱在一起,两个老女人相互打量着,一副相见恨晚的样子。嫂子说:弟妹呀,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
李大脚抹了一把老泪,哽咽道:受苦的不是我,是小莲啊,俺是半路上嫁到你家来的。
提起小莲,所有人的心情都复杂起来。在这之前,于守业已经把家里的情况在信里告诉了哥哥,于守大忙打断李大脚的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进了我们于家,就是我们于家的媳妇。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围坐在一起,跳跃着把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又重新细致的梳理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