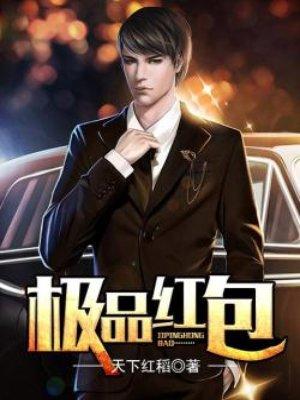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挪威森林歌曲伍佰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一直以来,我都自认为并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在和寻露告白的时候,我是真真切切地以为在这世界上我只喜欢她一人,再不会喜欢上别人;在云雾山旅馆答应她绝不辜负她的时候,我也是确确实实地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世间哪还有比她更动人心弦的女孩。
但我一直以来努力构建的一切,努力相信的一切,在沁河的这个黄昏,在萧蕾突如其来的一吻中,轰然倒塌。
&iddot;
我像失了魂一样浑浑噩噩地回了家,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睡。
和萧蕾接吻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苦痛,却用了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平复。
中考成绩也在假期中途放了出来,同我预想的一样,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英语、物理、生物、化学,全部一败涂地。
尤其英语,虽然选择题全涂了b,最后却只得了十五分,远低于百分之二十五的平均正确率,为此我在心里问候了无数次出题人的母亲。
到了选择高中的时刻,因为我的分数远低于任何高中的分数线,属于多交钱都没人要的范围。这次的选择权同样没有落到我手里。父母在经过几天的秘密商议之后,大体为我确定了一所中学,但是具体是哪一所,一直到开学前三天才告诉了我,并且他们一致决定‐‐从高中开始,让我放弃学习英语,改学日语。
&iddot;
就这样,我进入了市里的一所普通民办高中,过上了每天十点放学,早上六点起床,每个月只放两天假的&ldo;极为规律&rdo;的高中生活。
当然好处也是有的,就是学校离黑子和萧蕾所在的高中并不算远,步行也就二十分钟左右。另外教日语的女老师异常美丽温柔,很有日本传统女性的风范。
我也只有在日语课上能提起精神,勉强不睡觉,因为在她的身上我隐约可以找到某个过去的影子。
第一次日语考试,只考了简单的五十音图,相当于汉语拼音和英语的abcd,大体上就是考a后面是什么,d前面是什么。
几乎所有人都得了满分,就连坐在我旁边整天傻笑,开始我还以为有唐氏综合症的傻小子竟然都考了九十多分,而我,只考了十六分。就像一队伞兵排队高空跳伞一样,有的落在高山上,有的落在平原里,只有我掉在了粪坑里。
想想自己中考时,英语才考了十五,这次日语考十六,还算进步了一分,我心里也没有格外不舒服的感觉。只是美丽的日语老师被彻底地激怒了,她坚持认为这是对她辛苦教学成果的彻底否定和无情污蔑。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我进行了暴风骤雨般的批评,甚至到最后眼圈发红,几度哽咽。
尽管如此,她直到最后仍没有说出这个考了十六分的同学的名字,只是坚持以&ldo;某位同学&rdo;作为名字的代替,为此我心里极其难受,前所未有地对一位老师感到深沉的愧疚。
从那以后,我对学习日语格外用功。倒不是说这门语言有多重要,而是为了不让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女人为我掉眼泪。
☆、情难自己
&iddot;
入学一个月后,我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从宿舍搬了出去。
这要归功于学校良好的&ldo;住宿条件&rdo;。在不到十五平的空间里,他们竟然放下了五张床,上下铺,住进去了十个人,而且宿舍的窗户朝北,终年不见阳光。
我租的公寓在一个银行的家属院里,是一栋别墅的一楼。虽然房租略贵,离学校的距离也比较远,但因为房间干净,周围安静,最终还是选择了这里。
房东是个在银行工作的中年胖子,说话比较和气。别墅一共两层,大约两百平左右。一楼是客厅,摆着电视沙发等物件,从客厅往右拐有一间卧室,就是租给我的那间。二楼则全部租给了在附近工作的一个白领青年,他隔三差五地领着一个年轻女孩来住。我经常在半夜被楼上的叫-床声吵醒,虽然这给我带来了一定困扰,但是同八-九个人同时打呼噜的奏鸣曲相比,那声音简直舒服得要命。
&iddot;
我的房间里只有一张造型简单的欧式铁床,一张用过很多年的书桌和断掉了一条腿的椅子,四面白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古惑仔的陈旧海报。
在搬过去的第一天,我就买来了新的桌椅,把旧的搬到别墅的一角,并撕光了墙壁上所有的海报。在整理东西时,我不经意间从箱子里翻出吊桥上的那个黑色旅行袋来。我把它放到新买的桌子上,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还是打开看看。一方面对里面存放的东西好奇,另一方面期望着能从中发现什么线索,好联系死者家属。
我小心翼翼地拉开了旅行袋的拉链,发现里面除了一个硬邦邦的圆形纸筒以外,空无一物。
我拿出那个圆纸筒摆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了一会,最后思虑再三,还是揭开了纸筒一端封着的胶带。
最后从里面抽出一卷白色物体,从边缘溢出的各种颜料判断应该是一幅油画。画布被整齐地反卷着,我手忙脚乱地在桌上把油画完全展开,整幅画被保存得很好,颜料表面甚至没有一丝开裂。
在台灯下看清整幅画的瞬间,我感觉身体的气息在忽然间紊乱起来,手脚微微灼热,指尖发麻,心脏一直突突地跳个不停。那是一种让人上瘾的偷窥她人秘密的罪恶感与兴奋感交杂在一起的感觉。
油画中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正躺在一块猩红的法兰绒地毯上,她皮肤雪白,辱-房挺翘,就连黑色耻毛的粒子都被一一表现了出来,仿佛画家本人的意志不是在作画,而是在用画笔拍摄一幅高度清晰的写真一般。
那女子的五官谈不上漂亮,脸部轮廓也不甚完美,她轻松地交叠着双腿,仿佛有些无聊地把一缕黑发衔在嘴里,神态中微微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哀愁,或许是因为这幅画画了太久的缘故。
在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后,我长出了一口气,把油画反卷好放回画筒里,然后用胶带封好,放到床下的箱子里。
我对油画了解不多,但是那幅画中的女子却异常鲜明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我从画中察觉到了一种迷人的矛盾。
她不完美的五官,妩媚入骨的表情,比例协调的身材,疲惫哀愁的肉体,以及从这种肉体的束缚中所挤压出来的难以驯服的野性,都深深地感染了我。
&iddot;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在操场举行了全校大会。
会议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那天的会议异常得短,只开了两个小时不到,校长就宣布散会。
我左手拎起椅子,随着人流往教室方向走去,那天的阳光异常明媚,秋风异常温柔,我忽然想起一年前的那个秋日来,寻露侧脸的轮廓也慢慢在眼前浮现。她的微笑,她说话时细细的不紧不慢的声音,她火热的嘴唇,冰凉的手指,以及关于她存在过的一切证据,开始像cháo水一样朝我渐次袭来,从细浪白沙,到波涛汹涌。
走到教学楼前,这梦境瞬间戛然而止,我日思夜想的寻露还是没来,但是萧蕾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