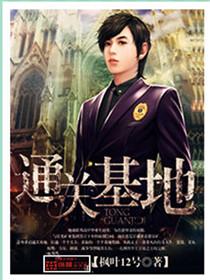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清欢百味棠岁 > 第118章(第1页)
第118章(第1页)
莫名其妙地,他忽然想起了新来的知县大人。
之前那些年来的知县大人,陶父陶母都会去送些钱送些礼物。左右陶公庙的香火实在是旺盛,聚敛的钱财几乎是个旁人难以想象的数字,陶公陶母又从不对外说,那些知县们不清楚底细,要的再多也不过是九牛一毛,陶父陶母倒也承受的住。而有了大笔钱财进账,再看陶公庙似乎也没什么要聚众揭竿起义的打算,往年的知县们也就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偏生今年新来的这个知县不大一样。
在他来之前,陶父陶母就把消息打探得清清楚楚了:是个年纪极轻的庶吉士,十几岁就中了榜,实在是个天纵奇才的,只是得罪了京里的大官儿,这才被放出来。
陶父陶母也不清楚官场的这些个东西,只是听说了是个年轻聪颖的进士,便觉着定是个厉害的,而且没准儿还有些年轻人特有的正直脾气,又听说出身不错,想必是该见的都见过了,因此送去的礼是厚了又厚,生怕金光晃不花这位新来的顾知县的眼似的。谁成想,这位新来的顾知县竟是半点儿面子也不给他们,连礼物是什么都没看,直接便把送礼的人给拒之门外了。
陶父陶母犯了愁,一商量,索性咬咬牙又把礼加厚了几分。这次倒是学聪明了,没直接上那俗之又俗的金子,而是托人买了些名贵的古玩字画,妥妥贴贴地收在红漆雕花的木箱子里送了过去。
然而结果与之前一般无二。
这样的一位知县,会不会想端平他们这个陶公庙呢?
陶斯有些出神地想着。
扪心自问,他和父母并没有做多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譬如起兵造反、颠覆王朝一类的,他们便是万万不敢的,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敢去想一想沾一沾。
他们做的最多的,也不过是在那些病痛缠身的人过来的时候说一些故弄玄虚的话语,最后等他们掏出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子之后,再给他们递上一杯符水——把一张被他胡乱画了些道道、然后烧成灰烬的符纸掺进水里的“符水”。
应该是没什么事的,他们愿意来,而他也只是给了他们他们想要的,陶斯想着。
只是那些奇奇怪怪的知县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喜欢为难他们而已。
陶父陶母不曾教过他什么旁的道理规矩,陶斯对于人世间的种种道理便也不甚了解。
他们只需要一个高台上的木偶。
而不论是否出自本心,陶斯也只是一个高台上的木偶。
上头的陶公大人许久不说话,王粟忍了又忍,到底还是没忍住,悄摸儿地抬了抬头,看向了那位大人。
大人正在出神。
或许是因为日光晦明变换,或许是他年事已高老眼昏花,不知怎么地,他竟仿佛在陶公大人的眼角看到了一滴晶莹。
王粟一瞬间,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恍惚间,在他面前高台之上的已不是那神秘莫测、高高在上的陶公大人,而是一个皮肤苍白、身形瘦削的少年,肩膀单薄得甚至撑不起那锦绣重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