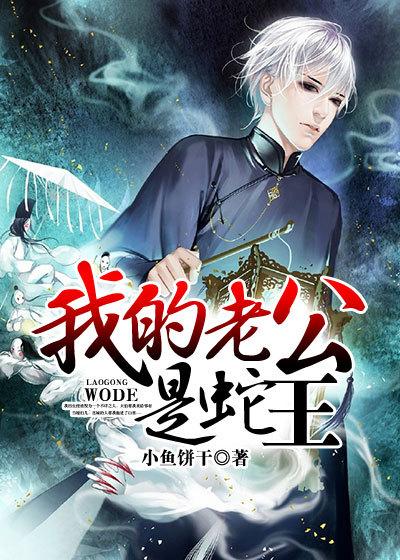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心如死灰后他们后悔了简介 > 第108章 if线十七母亲(第2页)
第108章 if线十七母亲(第2页)
还有每年的那个日期——他现在知道了那叫作“过年”。
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就会一个人在房间里,不见任何人,对着外面的花灯和烟火坐上一宿。
“没有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吗?”任霜梅轻声问。
“母亲的身体没有办法适应海上生活,又因为受伤和生下我,体质变得更弱。”
明危亭解释:“父亲只要还是明先生,就不能轻易下船。”
并不是因为什么古怪的规矩,只不过明家的“先生”担负的是公海势力的平衡。
这些年来,公海上的势力纷争一直激烈,随时都可能演变成冲突,必须要有人来出面压制调停。
只有彻底把这些势力驯服,明先生身上的枷锁才能够被卸掉。但要真正调停各方,让公海恢复平静,至少还要五六年的时间,如果期间发生了什么意外,或许还会更久。
……当然,这些理由也都只是最官方的说法。
至少禄叔是这么和年纪还小的明危亭说的。
禄叔悄悄跟他说,父亲找出这些理由,只是因为不敢去见母亲。
父亲不敢去见母亲,怕一见到母亲就忍不住带母亲走,也怕一念冲动,永远跟母亲留在岸上。
父亲怕见了母亲,惹母亲生气伤心,也怕两个人分开以后更难过。
禄叔还说,也可能是父亲怕母亲还生他的气——任何一个人被这么对待当然都要生气。
明危亭很同意这一点。他也觉得父亲这件事做得并不妥当,如果是他,他就会下船解释清楚缘由,劝说对方留在岸上。
禄叔问他:“要是见了面,发现人家执意要跟你走,哪怕身体再差、再不适应海上的生活,也不肯跟你分开呢?”
明危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自然也没考虑过这些,被这个问题难住,没能答得上来。
“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一辈子生活在船上。”
禄叔揽着他的肩膀,给他讲:“就连明家招募的人里,每年也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因为身体或是心理无法适应,不得不回到岸上。”
这种情况和先天的体质有关系,不是凭意志就能克服的。
禄叔给他举例子,就像有的人天生海鲜过敏,你不可能叫他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就把一条鱼平平安安地吃下去。
……
这就成了没办法的事。
如果两个人,一个注定只能留在岸上,一个注定要永远漂泊,分开就必然会发生。
“所以。”明家的总管给当时还小的明危亭讲这件事,语重心长地告诫年仅十岁的少当家,“一定要找个不晕船的爱人。”
年仅十岁的少当家把这些话严谨地记下来,又在多年后回去找父亲聊时,问起了这些事。
虚岁十七岁、周岁十五岁的明少当家没说完话,就被父亲扔回自己的船,还被父亲打着闪到眼花的灯语训了足足三十秒钟。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父亲的做法。觉得他古怪,像是撞了邪,忽然就变了脾气。”
明危亭说:“我后来长大了一些,听说了当初的事,也这样想过。”
“直到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些特殊的、不能完全用科学原理解释清楚的事。”
他解释完了事情的全部始末,稍一停顿,又继续说完最后一句:“……或许不是撞邪。”
骆炽听懂了他的意思,迎上明危亭的视线,指了指他又指指自己。
明危亭点了点头。
……或许和他们一样。
或许那场噩梦里,父亲永远失去了母亲。
“怪不得过年的时候也不高兴。”骆炽趴在桌沿,下颌抵着手臂,仔细想了想,“要是连过年的时候,我都见不到妈妈,我也会难过的。”
每次一到过年,任霜梅都会准时在零点给骆炽打视频电话,大年初一就会带着他出去逛庙会、放鞭炮,会让他彻底玩得尽兴。
妈妈是他最喜欢的人,所以骆炽想,这种感受大概也差不多。
“父亲是很难过。”明危亭说,“但我到现在,还是不赞同父亲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