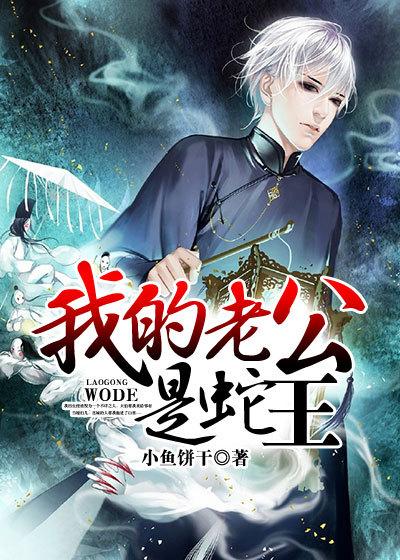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心如死灰后他们后悔了简介 > 第108章 if线十七母亲(第1页)
第108章 if线十七母亲(第1页)
很多时候,阴影会来得突然且不可预料。
就比如来邀请新朋友出海的明少当家。
……
直到离开船上岸前,明危亭都依然没能预料到,一把笤帚的震慑力能够到达这种地步。
直到骆炽做好了松仁玉米,一家人坐下来开始吃饭,明危亭都还极为谨慎地回答着任夫人的问题,每答一句话都会先留意火苗打过来的眼色。
“好了,又没那么严重。”
任霜梅把两个小朋友谨慎的交流看在眼里,没忍住笑,一人轻敲一下脑袋:“笤帚也不是随时都会用。”
她拿起一块点心,空着的手揉上火苗的头发:“再说,有人托我不要把你轰出门,我也答应了。”
明危亭道了谢,闻言怔了下:“是什么人?”
任霜梅和那孩子说好了要保密,笑着摇了摇头,拿起一个没用过的调羹,给明危亭的碗里加了勺松仁玉米。
“你还这么小,就帮家里跑船了吗?”
任霜梅扯开话题,问明危亭:“父母放不放心?”
明危亭放下筷子坐正,想了想,解释了自己的年龄。
如果按照出生日期算,他这个年龄的确很难服众。但明家计算年龄的方法和公海的习惯不同,出生就记一岁,过一年又算是一岁。
明危亭的生日在公历的一月份,所以这样算下来就是十七岁,已经是完全能跟船出海,能替父亲出面处理事务的年纪。
“算法父亲还没有教过我。”明危亭说,“每年增加一岁的日期都不一样,大多都是一月末到二月。”
他回忆了下:“那天船上的气氛会很热闹,到处都是灯笼,还有人放烟火。”
任霜梅听他相当复杂地解释了半天,和火苗交换了个视线,不由笑出来:“这不就是虚岁?”
明危亭抬起头:“虚岁?”
“虚岁就是这么算的。”骆炽给他解释,“因为十月怀胎,所以生下来就有一岁,每年的大年初又一长一岁。”
任霜梅点了点头:“你说的那天就是过年,这在岸上是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一家人都要团团圆圆,祈福平安。”
明危亭蹙了下眉。
他完全不了解这些知识,专心听着,认真记下来。
任霜梅看着他的神色,沉吟了一会儿,忽然问明危亭:“妈妈是什么样的人?”
“不清楚。”明危亭说,“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把母亲送回岸上了。”
明危亭听禄叔说起过这件事。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原本非常好,只是母亲一直不能完全适应船上的生活,又在之前公海势力纷争的冲突里为父亲挡枪受过伤,身体始终都不好。
在生下他之后,母亲就变得比之前更虚弱,大半的时间都在船舱里养病。
听禄叔说,有天晚上,父亲似乎做了场非常可怕的噩梦。
那天原本该是母亲回娘家的最后一天,父亲约好了去接母亲,船要泊进港口的当晚。
在深夜里,父亲忽然喊着母亲的名字惊醒,在船上到处疯了一样找母亲,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禄叔赶过来的时候,看见父亲已经冷静下来,一个人在船舷边抽烟。
……那天的船没有泊港。
那条航线后来取消了,那个码头也因为经营不善废弃,不再有船在那个港口停泊。
任霜梅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听到这里停下筷子,皱起眉:“妈妈没被接走?”
明危亭摇了摇头。
那个时候的他年纪还很小,相关的记忆已经很模糊。
他只记得,那之后的父亲就忽然像是变了个人。
父亲不接母亲打来的电话,不回复任何消息,除了做明先生该做的事,剩下的时间就都只是对着窗外平静的海面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