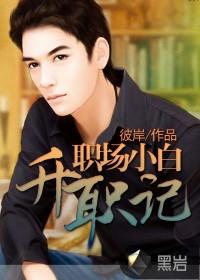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我欲扬明浴池戏春春情春意 > 第二十五章 京师乱(第1页)
第二十五章 京师乱(第1页)
6树德头七过后三日,都察院御史叶樘上了一道疏,参奏翰林院掌院学士陈以勤仗势凌辱职官司曹,挟私泄愤逼死人命。其理由有三:其一,自6树德弹劾陈以勤后,陈以勤策动门生故吏日夜守在6树德家门口叫嚣叱骂,吓得6树德躲在家中多日不敢出门,最后被逼无奈之下,终于含恨自尽;其二,陈以勤鼓动一干不明真相的官员连上弹章奏本,逼迫君父对6树德从重论处,6树德觉得百口难辩,便咬破手指,在邸报所登的劾文之上写满了“冤”字;其三,6树德虽被逼死,临终之时却还不忘向君父尽忠向朝廷效命,将其弹劾陈以勤奏本的草稿悬挂在胸前,一是以死明志,二来也是尸谏,以示至死不改其不与陈以勤这种辜负圣恩欺凌朝廷命官的小人同流合污的初衷。
所谓死无对证大概就是这种情形,任谁都觉得叶樘的说法颇有牵强附会之处,可谁也拿不出确凿的反驳证据。何况御史有风闻奏事之权,朝廷律法赋予他们随意展开联想并随意批评指责任何人的权力!尤其是他所说的第三条证据,国朝此前也有过先例:就在武宗正德帝时期,权阉刘瑾祸国乱政,又在东厂、西厂之上更设立内行厂,严密监视百官,肆意凌辱朝臣,户科都给事中许天赐想弹劾他,奏疏已经写好后却不敢投递通政使司,便将奏疏揣在怀中,悬梁自尽以明心志,劝谏君父。此事相去不远,6树德又是翰林院史官,曾参与为武宗先帝修《实录》,他投缳之时将弹劾陈以勤的奏疏装袋悬挂于胸前,焉知他不是效仿许天赐之例,想以死来抗争陈以勤及其门下对自己的欺凌和侮辱?!
百口难辩的陈以勤再次被气得吐血卧床不起,他的门生故吏咽不下这口气,纷纷上疏弹劾参奏叶樘行事乖张、攀附权贵及索贿贪墨等秽迹。
叶樘是严嵩的门生,说他攀附权贵便是扫了严嵩一笔。严嵩如今虽然失爱于君父,被逐出内阁改任闲差,但毕竟是当过多年礼部尚书主持过多次科考之人,还于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夏言被皇上革职斥退后,虽未明确继任辅,却在实际主持过内阁全面工作三、四个月,也照样有一干门生故吏充斥朝堂,那些人自然不会置之不理,便愤然而起为叶樘抗辩。怎奈叶樘为官确有不检点之处,那些人想明着帮他说话显得力不从心,不得不转而攻讦陈以勤门生故吏的种种失职举止及违礼言行。
以夏言为的内阁学士以及前一段时间去过陈以勤府上探望以示慰问的当朝大员既替陈以勤抱不平,又惋惜于不幸亡故的6树德,此时已心神大乱,加之他们都知道严嵩与陈以勤两人积怨由来已久,在6树德头七公祭之日陈以勤的门生又殴打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两人旧恨未消又添新仇,便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各自约束门下不得介入这场意气之争,任由两帮人笔来墨往打了个不亦乐乎。
陈以勤资历虽老,官运却不是很顺,门下没有多少得力干将,加之他本就不是善于党争之人,时下又缠绵病榻,自然对门生故吏的反击事宜不能谋划妥当,翰林院那帮涉足官场不久的愣头青词臣们渐渐在这场纷争之中落了下风,有人气不过就上了一道奏疏,直接弹劾严嵩贪赃枉法,弄权乱政。
因6树德一事,陈以勤是当其冲之人,被严嵩门下指责斥骂也是没有办法,但严嵩却一直隐匿在幕后,因其门下之过就弹劾他,显得有些牵强,加之严嵩早就已经远离政治中心,翻旧账炒冷饭之举非但没有杀伤力,更引了严嵩门下的激烈反弹,不但京城六部等各大衙门的京官连上弹章奏本,严嵩遍布两京一十三省的门生故吏也纷纷起而攻讦陈以勤。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严嵩当日对儿子严世蕃所说的“为官三思”要旨的精妙了——严嵩这两年韬光养晦,一直在埋头缮抄辑录《永乐大典》,没有多少错处能被人揪住不放;而陈以勤就不同了,再修身持谨,毕竟也是六部九卿之一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朝议之时总要奏事言,以他的迂腐不思变通的性格,多有不当上意之处;即便没有,这些年来的高头讲章总有几处疏漏,与同僚属下晤谈宴饮之时总有有失官仪甚或非议朝政的时候,严嵩执掌翰林院也有五、六年之久,陈以勤的这些过错自然有人会透露给严嵩门下,成为新一轮弹劾的炮弹。
越落了下风的陈以勤门生们更不服气了,接着就犯下了另一个大错——将严嵩当年执掌礼部之时逢迎君上,恭撰青词而得以入阁拜相的丑事再一次翻了出来大炒特炒!
也只有这帮翰林院的书呆子敢这样想敢这样做,他们只知道严嵩失宠是因为皇上已经幡然醒悟不再一意玄修,却忘记了青词宰相可不止严嵩一人,时下正任内阁辅的夏言便也是一位青词宰相!
夏言自然不会与他们这些微末小吏计较,也约束亲近的门生故吏不必理会,但他总不能明邸报告示朝臣,那些根本就与夏言没有密切关系却想巴结他的官员不会熟视无睹,也愤然加入了声讨陈以勤的行列。待夏言现之时,有的弹章已经递交通政使司转司礼监呈御览。
弹章奏本雪片一样涌进大内,就杳无音讯。所有人都知道是被皇上“淹”了——明朝皇帝有个极恶劣的毛病,遇到臣子所上的奏疏不合自己的心意却又不好辩驳或是降罪于这个建言的官员,就把它留中不。重重禁宫深似海,这份奏疏从此就再无下文,内阁和六部也就再也看不到,朝臣们戏称之为“淹”。
当然也有可能是皇上根本就来不及看,但当事双方却不敢做如此之想,因为这种通常被“淹”的奏疏还有更大的一种可能是圣意已为之所动却还在犹豫不决。皇上两难取舍之时,比的便是谁的攻击更为犀利,那些两榜进士出身的官员在这方面眼光的敏锐和手段的毒辣一点也不比久经沙场的武将差。
又是雪片一样的弹章奏本涌进大内。
严嵩集团和那些想攀附夏言的官员分进合击,攻势异常迅猛,陈以勤的那帮门生完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全面崩溃只在旦夕之间,这个时候,突然又杀出来了一股强援——尊礼派。
自左顺门事件之后,尊礼派大批中坚力量被斥退罢黜,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其后更在嘉靖帝和把持朝政的议礼派两方联手、刻意打压下,势力急剧萎缩,时下只有硕果仅存的内阁阁员、礼部尚书高仪和侍郎杨慎两位大员苦苦支撑着局面。以他们的实力,根本不足以与骤然兴起于嘉靖初年并把持朝政十几年的议礼派抗衡,但由于他们毕竟代表着孔孟门徒最为看重的礼仪道统,得到了不少中低级官员和士林清流的同情和支持,而这些人又与以清流习气著称的翰林院那帮词臣同气连枝,如今见到翰林院的清流在严党攻讦之下处境岌岌可危,自然要以义气为重,广为声援。
这场纷乱的意气之争在尊礼派一位都察院御史上疏参奏严嵩之后,变得越的混乱起来。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多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除了在拜谒显陵之后极言祥瑞,被官场士林耻笑之外,并没有过深地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由于他已得夏言举荐升任礼部尚书,在为嘉靖生父兴献帝上尊号配享太庙这件大事上再也躲不过去,就铁了心地不惜背上骂名,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安排了极其隆重的礼仪典礼,并充分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成为宣告皇上赢得大礼仪之争全面胜利的一曲颂歌。他也从此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对嘉靖言听计从,也得以平步青云,更被人们视为议礼派后期崛起的一位大将。因此,在议礼派的官员看来,严嵩虽为人卑劣,曾以阴谋将夏言赶出朝堂,但这终归是本派内部之事,尊礼派的人攻讦他便是借机向本派难,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将矛头又对准了尊礼派。
议礼、尊礼两派的领袖人物对皇上起复尊礼派的用心看得很清楚,为了不给对方留下先难的口实,平日里拱手作揖点头微笑,总也能保持着表面上的和睦,但事态展到如此混乱的地步,无论是夏言还是高仪,心中都是叫苦不迭,但他们都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只能约束门生亲信不得将矛头直接直向对方头面人物,至于是否会波及对方门下,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