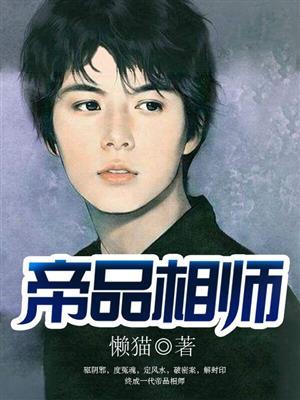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被虐后遗症叫什么 > 第85页(第1页)
第85页(第1页)
祁宴深蹲下身子,用手扒开他捂着额头的手,往伤口那看了两眼。没流血,就是有点肿了。他假惺惺地揉了揉伤口,往那吹了两下,笑着说道:“真是心疼死我了,赶紧上楼,我给你包扎一下。”余真再也不会信这人的鬼话,酝酿了两秒后,立马虚软着步子,想跑开。跟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似的,他拼命的逃着,祁宴深就追了上去。好不容易终于快到了房间,祁宴深又一脚,毫不留情地踹在了他的后腿根上。余真瘫倒在地,痛苦的呻吟了下。“还敢跑?你以为你跑得掉?”“唔……”祁宴深用手抓起他的头发丝,往屋里拽去,然后将门反锁关了个彻底。头皮整块被薅的发麻。祁宴深往四周转了下,跟当自己家一样随意慵懒,像在寻找着什么蛛丝马迹。“你晚上在这睡觉?跟那姓靳的,做了吗?”余真从地上爬起,往后缩了点,战战兢兢道:“你别想的那么龌龊,我跟他什么都没有。”祁宴深看他一副担惊受怕样,又将手指往对方脸上勾勒了过去,笑的意味深长,“口说无凭,我要来验验身。”爽了还是疼了【已改】“你别乱来,祁宴深,这是在靳家。要是让人知道了我们的关系,你也会颜面扫地的。”余真试图去警告对方,可那语气却因不够凶狠,反而还让人感觉不痛不痒的,心头冒起了软尖。那张巴掌大的脸,被留长的乌发遮掩了些许棱角,衬得那皮肤冷的胜雪。这人明明是个男孩,却比女孩还要生的眉眼昳丽,唇红齿白。这模样入了祁宴深矜贵的眼,不禁心里滋生出了想糟蹋,蹂躏人的念头。但又觉得要慢慢玩。那张俊美如芝兰玉树的面孔,散出点霁风清月的笑,他不以为然的说道:“我们家宝贝,学会威胁人了呢?这也是那姓靳的,教你的?”靳迟迷途知返,祈求他的原谅与爱意,可祁宴深不会。“够了,祁宴深,别再提起他了,我已经说过我跟靳迟,一点关系都没有。”余真故作镇定,去掩饰内心戛然而生的局促不安,可越是这样,就越显得捉襟见肘了起来。祁宴深一眼看出他的小心思,将笑容慢慢的敛着收了回来,缓声道:“哦?要是没关系,你还上赶着住进他家了?”对方的脚步往余真那逼仄去,嗅着他身上的味道,彼时睨着的眸子,视线陡然出一抹冷锐的芒色,似乎是厌烦对方的肉体,沾染上了别人的味道。“你可别说,是他强迫你,把你关这的。”祁宴深懒得跟他扯皮,有点不耐烦。听完这话,余真紧张的吞咽了下唾沫,往后边又缩了点过去,直到无路可退。吭的下,他的背脊被抵到冰冷的玻璃边,顿时生了股凉意。他一字一顿的说,“信不信由你。”余真抬起眼去看祁宴深,神色中透出股浑然而生的病态,破碎之感,如夜空挂着的一轮残月,清冷又孤傲。正常人会觉得月亮遥不可及,可没心没肺的孽畜,却总想着将其采撷下来亵渎。祁宴深笑的发冷,掐上他的下颚,问,“你这什么态度?是不是在外边浪了两圈,都不知道谁是你的主了?”“我没有。”知道下一秒对方就要发火了,余真不想再把事情闹大,于是又立马示弱将姿态软了下来,不再硬碰硬的对峙。“你倒是能耐大,本事强,这勾引人,那勾引人的,把我弟都使唤的动,连给你偷钥匙开锁这种事都做的出来?”祁宴深不理睬,勾着唇笑,用手背拍了拍他的脸,恫吓的意味很深,又带着点挑逗,“看来我真的是,小瞧你了。”祁宴宁救余真,也是因为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对方受尽了非人的虐待,这才于心不忍,秉持着最后一点悲悯的良心,想将其从苦海中救出来。他确实没有使唤祁宴宁,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还是对方自愿的。但此刻余真缄口不言,紧闭双唇,愣是咬着牙一个字都不讲。生怕越描越黑。“说话啊,装聋作哑什么?”那双眼被酒气浸染的猩红,他将声音放低了下来,一股酒味,就这么卷袭上了余真的鼻腔,呛得人想咳嗽。薄薄的嘴皮被咬破了些,余真低了低眼帘,煽了煽薄如蝉翼的睫羽,才哑着嗓音,有点委屈的哽咽着,“你天天关着我,不让我出去,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太怕了,才跑的。”祁宴深知道他在装,但也没明着挑破对方的故作可怜,还觉得有趣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