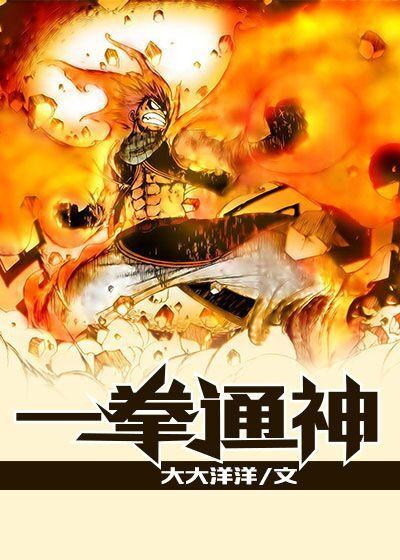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吾师晋江 > 第14页(第1页)
第14页(第1页)
到回国过后,陈轲就变这样了。常常一跪就半个通夜,跪到不知什么时候睡在地上,人事不省。
·
吃过饭,何景深难得散漫地坐了一会。
他不抽烟,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叠。不急着一定做什么,所以坐在这里,就这样看向窗外。
也不必想什么,就随便看看。
视线从他的角度延伸,恰好能看见数里之外的跨江大桥。夜幕下大桥总亮着灯,美成一道奇绝的风景。
然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让人获得暂时的安宁。烦躁的,麻木的,揪心而刺痛的,都一齐被抚整平息。
不过多时,他开口说话。
声音因平静而柔如江水,带着一种特有的质感,沉厚而温和。
“面放凉了不好。你什么时候起来,我再给你煮。”
灯下的人轻轻一颤。
何景深斜眸,恰好捕捉到这丝微弱的动静,不着痕迹地笑了那一下。
“差不多就行了,别老和自己过不去。”
他从餐椅上起身。一摞把餐具堆进水槽,擦过桌子又进了书房,关上房门。
八点十五。不知是有什么事,何景深出来一趟。
恰好目睹陈轲爬上沙发的过程。
赶忙上前来帮了一把,拽着人胳膊上了沙发。然后便迎上陈轲的笑,一丝慌乱下歉意的笑。
“想通了?”何景深问。看见茶几上的文件袋,弯腰拿手里。
陈轲点头,埋进臂弯喘息不已。他跪不住了,实在跪不住,再跪下去只会给老师添麻烦。这也能算是想通吧。
盘点装订整齐的文件,取出正好需要的那一份——2018年度职称评定通知——垫着文件袋翻上两页。稍一抬眼,便看见陈轲身上那些伤:殷红的,青紫的,当中凝着几道血迹,交错蜿蜒,令人心惊。
何景深不禁就蹙了眉,“等会。别动。”
陈轲又点头,“嗯。”
放下东西对直进厨房,洗手,取冰袋,拆开纱布和双氧水的包装,回到客厅又翻出药盒,给陈轲治伤。
过程都很熟悉,疼痛也很熟悉——陈轲咬着抱枕,直接给疼得脱了力,浑身透湿。
何景深递来两粒白药,陈轲没动。
索性把胶囊塞嘴里,喂陈轲喝水。
那双眼终于慢慢睁开,眉头舒展,水光里竟一抹淡淡的笑。唇畔牵扯,喉结耸动,口型似乎是一个谢字。
何景深颔首,表示他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