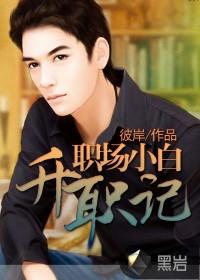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白羊by txt > 第46页(第1页)
第46页(第1页)
“梁在野,咱们结婚这么些年了。”唐宁盯着他,目光又转移到梁如琢身上,“自从踏进梁家的门,你就没把我当过自己人。你们梁家的传统就是找小三儿吗?”
梁如琢挑眉,似笑非笑地望着她:“唐小姐,就事论事吧。”
梁在野吐了口烟气:“唐宁,说话难听这性子像我。”
文羚站在一边,像一个局外人那样目睹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老实说在还不认识梁在野的时候,他与唐宁就已经彻底闹翻了,起因诸多,但导火索是唐宁自作主张把他们还有两个月就出生的小女儿流掉了,那是个很健康的女孩子,被亲生母亲强行剥夺出世资格居然就因为她是个女孩。
这件事让文羚被震撼了。
他忍不住打断他们的谈话,对唐宁大声说“离婚全是你的错”。
当然并不是,感情的破裂总是由无数客观和主观的复杂因素组成,但就像不知情的局外人一致认为离婚都是梁在野的错一样,他也有理由认为离婚全是唐宁的错,并且把这个理由平静、流畅地大声说给在场每一个人听。
会客室里安静了几秒钟,梁家兄弟的目光全都诧异地落在文羚身上。
唐宁恼羞成怒,踩着细跟高跟鞋站起来,毫无风度地扬起巴掌,尖声道:“你还没说够吗!”
她戴的宝石戒指从文羚下颌上刮了过去,梁如琢见势立刻把文羚拽到自己身边,梁在野抓住唐宁的手腕,拖着她到宅子外边,带她回公司谈,少在家里闹事。
临走梁在野回头看了一眼文羚,文羚躲在他弟弟身后,有点委屈,也有点勇敢。纷乱的雪片在玻璃上砸出轻巧的声响,窗外的淡光让那张苍白的小脸显得有些憔悴弱气,但看起来和第一次见他时一样澄澈,他有一双对世界同时抱着批判和讨好的眼睛,是独一无二的。
第30章
会客室重归寂静,梁如琢蹲下来查看小嫂子下颌被戒指划出的伤痕,伤口不深,但在渗血。
文羚坐在沙发上,绞着手指笑:“你生气了?”
“不宝贝你不应该掺合这件事。”梁如琢站了起来,从兜里摸出片创可贴给文羚贴在划痕上,“唐家曾经涉黑,国家正在扫除他们,老大又把他们往绝处逼,迟早会狗急跳墙的。你没有必要承受不属于你的后果,答应我别再提了,让我们处理好吗。”
“涉黑?”
梁如琢抿了抿唇,刚刚因为着急而失言了。
“可是关系到你在国内的发展。”文羚乖坐在沙发上仰起头,“我想让你留下,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一刀捅了唐小姐就能解决问题,我就去为你们做,可是这解决不了问题,我根本不在你们的世界,你们也从不让我走进去,我在乎谁对谁错吗,不在乎,这就像观看游戏一样,我想让你们赢而已。”
梁如琢扶着他的肩膀愣住了。妈的,瞧瞧这张让丢勒提香见过也会非他不画的脸都说了些什么。
文羚咯咯直笑:“你今天好像有别的工作,我不留你吃饭了。”说不准梁在野什么时候就会回来,他不敢拿这个赌。
梁如琢想多留一会儿,直觉让他认为他应该多陪一会小嫂子。如果小嫂子爱的是大哥,那么他刚刚一定受到了伤害,即使他不爱大哥,他也确实受了伤。
但他被小嫂子送上了自己的车。
文羚折了一支院子里的蜡梅花从车窗递了进来,笑容纯澈得就像蜡梅上的雪花。这场告别就像他们爱情开始的那样悄无声息,梁在野回来了,嫂子仍然要像攀附巨树的藤蔓一样靠大哥生活。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梁如琢如愿在他惹人怜爱的身体上套上大哥的衬衫,用大哥的领带把他的眼睛遮住,在大哥的床上上了小嫂子一整夜。
他问嫂子在大哥身边过得苦不苦,小嫂子说,人这种卑劣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谁最会欺骗自己,谁就能过得最快活。
说完嫂子就笑了,然后用香软的小舌头去勾他的喉结:“开玩笑的,这是我看书读到的句子,你不觉得很美吗。”
“并不美,它很残酷。”并且不会因为从一位美人口中说出来就减少一丝一毫的残酷,梁如琢只好更深地吻他干他救赎他,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让嫂子享受自己给予他的罪与罚。
他抓住了嫂子伸进来的手,像抓住了停靠在篱笆上的蝴蝶。他攥着兜里的金属物件,又犹豫着松开了手——明明想在嫂子身上留下自己曾经存在过的记号,却没有这个立场。
抵死缠绵的温馨十二月,这是梁如琢最愉悦的一个冬天,救世者与欺世者的角色他全部都体会过了。
他清醒过来时已经在工作台边发了很久的呆,那支梅花还插在他上衣兜里。同事们在工作台边围了一圈,大眼瞪小眼观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