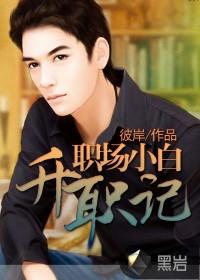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护士杀医事件2019 > 第45章(第1页)
第45章(第1页)
但是泰勒小姐对主席的影响,以及因此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影响有多大,人们也说不准。大家只知道这使得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大为光火,因为这大大地降低了他的作用。但兴建会诊大夫的独立餐厅对他很有利,他坚决拥护。
如果说其他人员因此被迫亲密相处,那最终他们可没能亲密起来,等级制度的存在依然显而易见。巨大的餐厅被划分为许多小的进餐区域,用花格屏障和栽种在木桶里的植物分隔开来。在每一间小室里,餐室的隐秘气氛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罗尔芙护士长将鲽鱼和薯片放在托盘里,来到桌边。过去八年来,这张桌子一直是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吉尔瑞护士长共享的。她把坐在这个奇怪世界里的外人看了一圈。最靠近门边的凹室里坐着实验室的技师们,他们穿着沾了污渍的工作服,在那里生气勃勃、吵吵闹闹地吃喝着。紧挨着他们的是门诊部的药剂师老弗莱明,他用他那沾满了尼古丁的手指将面包搓成药丸般的小球。下一张桌子上坐着四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医务速记员。高级文书赖特小姐,她已在约翰&iddot;卡朋达医院工作20年了,她像往常一样,正偷偷摸摸地快速吃着,一心想尽快回到她的打字机旁。临近的花格子屏障后面是一小群非专业人员:放射室的主管班扬小姐、医院社工主管内森太太,还有两个理疗室的工作人员。他们不急不忙地吃着,营造出一种平静的氛围,小心地维护着他们的地位。他们明显对于在吃的食物毫无兴趣,选择这张桌子,则是为了尽可能远离办公室的低级人员。
他们在想什么呢?大概是法伦的事吧。现在医院里上至会诊大夫,下至病房女工,不可能还有人不知道南丁格尔大楼发生了第二起神秘的命案,苏格兰场的人都已经来了。法伦的死大概是今天上午大多数餐桌上正在议论的话题。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吃他们的饭或继续干他们的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有那么多重要的问题要操心,还有那么多的绯闻要传,而这并不仅仅因为生活还得继续。在医院里,人们说起「生活还得继续」这句陈词滥调总是特别地意味深长。生活的确在进行着,出生和死亡以排山倒海的势头推动着它前进。新登记入院的进来了,救护车每天从急救室出发,手术单被签发,死人被抬走,痊愈者出院。一位年轻的护理学学生见过的死亡‐‐甚至突然死亡和意外死亡‐‐比最有经验的高级侦探还多。死亡叫人震惊的力量是有限的。学生们要么在第一学年就和死亡达成妥协,要么就放弃做护士。凶杀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凶杀仍然具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惊。但是在南丁格尔大楼,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佩尔斯和法伦是被谋杀的呢?恐怕苏格兰场那个神奇人物和他的随从不可能一出面就使人相信这个异常的想法。还有太多其他可能的解释,它们都比谋杀更简单、更令人信服。达格利什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要证实它却是另一回事了。
罗尔芙护士长低下头,漠然地切着鲽鱼。她没有什么胃口。空气里满是食物的浓烈气味,让人反胃。餐厅的嘈杂敲击着她的耳膜,无休无止,无法逃避,形成一团驱不散、赶不走的混沌,连绵不绝,个人的声音夹在里面很难听得清。
挨着她坐的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她将斗篷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背后的座位上,那个和她形影不离、已经走形的织锦手提袋砰的一声落在她脚下。她恶狠狠地吃着清蒸鳕鱼和欧芹色拉,彷佛在怨恨人为什么要吃饭,于是将怨气都发泄在食物上。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总是一成不变地选择清蒸鳕鱼。看着她吃鳕鱼,罗尔芙护士长突然觉得自己再也吃不下去了。
她提醒自己,没有理由一定得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去别处用餐,这个坚定的意志会使她拿着托盘走到三英尺之外的另一张餐桌上去,可这一简单的动作会成为一个无法挽回也无法改变的灾难。她左边的吉尔瑞护士长在摆弄炖牛排,把楔形的白菜叶剁成整整齐齐的正方形。一旦她开始吃,就会像个馋嘴的女学生那样贪婪。但她分泌唾液的餐前准备显得过分讲究。罗尔芙护士长想起自己曾多少次压制住冲动,咽下差点脱口而出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吉尔瑞,别弄了,快吃了吧!」毫无疑问,总有一天她会说出来。那时,另一位讨人厌的中年护士长就会宣称:「她只会越来越别扭,大概是年龄的缘故。」
她也考虑过从医院里搬出去。这是允许的,她的经济实力也负担得起。买一套公寓或小屋子是她为退休生活所做的最好投资。但是朱莉娅&iddot;帕多只用几句不咸不淡的摧毁性评论就把这个念头赶走了,那些话像几颗冰冷的石子,掉进了她希望和计划的深潭。罗尔芙护士长还记得她那孩子气的尖细嗓音。
「搬出去?你为什么想那样做?那样一来我们俩就不能经常见面了。」
「但我们应该这样做,朱莉娅。我们能有更多私人空间,不必再冒现在的风险,也不必再去骗人了。我会买一栋舒适宜人的小屋子,你会喜欢的。」
「那总不如现在方便,当我想要的时候就可以到楼上去看你。」
当她想要的时候?她想要什么?罗尔芙护士长拚命从脑子里赶走这个她绝不敢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