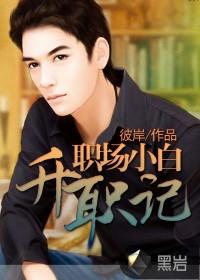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护士被杀害 > 第38章(第1页)
第38章(第1页)
他突然产生一阵冲动:「我想你大概比这里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佩尔斯护士,可能十分了解。我不相信她是自杀的,你也不相信。我要你把关于她的一切都告诉我,那会帮助我找出一个动机来。」
一秒钟的停顿。这是他的想象,还是她真的在下决心说什么事呢?然后她开始说,音调挺高,却有种不善表达的孩子气:「我猜她在讹诈某个人,她对我干过一次。」
「说说看。」
她用探究的目光看着他,彷佛在估量他的可信度,或者是在衡量这件事值不值得讲出来。然后她的嘴角上翘,露出一个微笑,好像在缅怀往事,接着平静地说道:「一年以前我的男友曾和我在一起过了一夜,不是在这里,是在综合护士宿舍。我打开了一扇防火通道门放他进来。我们当时只是闹着玩的。」
「他是约翰&iddot;卡朋达的人吗?」
「嗯,是的,是外科登记处的。」
「那么希瑟&iddot;佩尔斯是如何发现的呢?」
「那是我们预考‐‐就是第一次国家注册考试‐‐的前一晚。佩尔斯每逢考试之前都要闹肚子。我猜她是沿着走廊慢慢摸到厕所去时看见了我正让奈杰尔进来,又或许是她返回卧室时在我的房门上偷听来着。她大概听到了我们在房中咯咯地笑,或者诸如此类的声音。我料想她听了个够。我不知道她这样干是要做什么。从来就没有人想和佩尔斯做爱,所以我想她就是要听别人和男人在床上的动静以获得一点刺激。不管怎样,第二天一早她就跟我说了这件事,还威胁说要告诉总护士长,把我赶出护士培训学校。」
帕多说这些话时并无怨恨的语气,还几乎觉得有一点好玩。这件事当时没有惹恼她,现在也没有惹恼她。
达格利什问:「她问你要多少钱来买得她的沉默?」
他毫不怀疑,不管她要了多少钱,那笔钱一定没有支付。
「她说她还没有打定主意要什么,得想一想,得要得合情合理。你真该看看她当时的那张脸,斑斑驳驳,红得就像一只令人讨厌的火鸡。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拉长着一张脸的。我假装害怕极了,后悔得要死,要求那天晚上我们应该谈一谈。那样做是为了给我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去和奈杰尔联系。他和他守寡的母亲就住在城外。她很溺爱他,我知道叫她证明她儿子在家里过的夜毫不困难。她甚至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她认为她宝贝的奈杰尔想要什么就该得到什么。但是我得赶在佩尔斯之前把一切安排好。那晚我见到她时,告诉她我们两人坚决否认那件事的存在,奈杰尔有不在场证据来支持他。她忘了奈杰尔还有个母亲,也忘了别的事。奈杰尔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侄子。如果她去告了状,也只有她会被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赶出去,而不是我。佩尔斯真是蠢得要命,真的。」
「看来你应付起这类事来得心应手、镇静自如,真叫人佩服。你就真的不知道佩尔斯打算怎么惩罚你吗?」
「啊,我当然知道!我在开口告诉她之前先让她说出来了。真是有趣极了。那根本就不是惩罚,更像是讹诈。她想和我们玩,加入我们这一伙!」
「你们这一伙?」
「嗯,就是我、詹妮弗&iddot;布莱恩和黛安娜&iddot;哈泼。我那时正和奈杰尔交往,黛安娜和詹妮弗的男友都是奈杰尔的朋友。你没见过詹妮弗,她就是那些因流感而请假的学生中的一员。佩尔斯要我们为她介绍一个男朋友,那样她就能成为我们这一伙人中的第四个了。」
「你不觉得这很令人吃惊吗?从我听到的有关她的情况来看,希瑟&iddot;佩尔斯根本就不是那类对性有兴趣的人。」
「人人都对性有兴趣,只是各有各的方式。佩尔斯只是没有直接提出来罢了。她说我们三个她都信不过,应该另找一个可靠的人来监督我们。猜猜看!猜中了是谁可没有奖金!我知道她想要谁。是汤姆&iddot;迈利克斯,他那时候是儿科的登记员。他一身缺点,相当令人讨厌,但是佩尔斯喜欢他。他们俩都属于医院教友会的,汤姆在这里待满两年之后就要去当传教士什么的。他倒是很适合佩尔斯。我敢说只要我对他施加压力,他完全可能和她出去幽会一两次。但那样做对她没有一点好处。他不要佩尔斯,他要的是我。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达格利什当然知道,毕竟这是最普通、最老套的个人悲剧。你爱一个人,他却不爱你。更糟糕的是,他不惜舍弃自己的最大利益,也要打破你平静的心境,去爱上另一个人。假设没有了这种人间悲喜剧,世界上半数的诗人和小说家又该干什么去呢?但是朱莉娅&iddot;帕多不为所动。达格利什想,如果她的声音里有一丝同情,甚至是表现出一点儿兴趣就好了!佩尔斯这种不顾一切的需求和对爱的渴望迫使她从可悲的乞求者走向了讹诈犯,但她在被讹诈者那里却一无所获,甚至连一丝觉得好笑的轻蔑也没有。
这个被讹诈者甚至都不觉得有必要要求佩尔斯保守秘密。她此时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便把原因告诉了他。
「我现在不在乎你知道了。我干吗要在乎?毕竟佩尔斯死了,法伦也死了。我的意思是,这里出了两宗命案,总护士长和医院管理委员会有更重要的事得操心,哪里还会管我和奈杰尔上床的事。可是每当我想起那个晚上,那才叫销魂呢!那张床太窄,一直吱吱嘎嘎地叫,奈杰尔和我咯咯地笑着,我们几乎不能够……可是只要一想到佩尔斯盯在锁洞上的那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