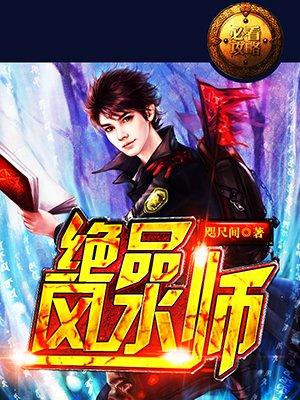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戏梦番外辉月生辰 > 第86页(第1页)
第86页(第1页)
刚才行云走得匆忙,应该不是他吧。可是木痕犹新,指印宛然。这个人的指头一定很修长。子霏缩回手来,食指上沾了一点红。咦?那个人被木刺扎破了手吧。血都沾在这里了。风吹在脸颊上,热热的痛被凉风吹得妥贴舒适了些。只是同榻共眠,行云至于生这么大气么?摇摇头,又是想气又是想笑。仔细认了道路,向着帝都宫城的方向去。观花鞭马,醉酒折香。行云这样快乐而无忧的生活,让他有些羡慕。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这样的渴望见到辉月。迫切而强烈的愿望,冲动得难以克制。子霏捂着胸口,步子慢了下来。觉得胸口闷痛。那种沉钝的,压抑的痛楚,子霏所熟悉的痛楚,慢慢的扩散。要命。怎么不早不迟偏在这里。前无村后无店,甚至一个行人也碰不到。他捂着胸口慢慢靠着树坐倒。这个旧伤,恐怕永远也好不了。当时气急焦躁,拖着破败的身体,从隐龙折返天城,扑空。再追至帝都。风云色变的上界,血流千里的帝都。早也想过,无人相助,杨沃迟不可能一个人死里逃生,再潜踪那样久,最后捉到那一个空子来寻隙为凶。奔雷曾经怀疑是七神。但是七神已经尽被那时的飞天屠戮杀死。谁也没有想到,是克伽。突变猝生,奔雷身负重伤,星华与平舟远在西隅鞭长莫及,辉月独木难支。什么风花雪月的话也放到一边,在危机四伏的困境中,什么也来不及去想去说。同舟共济,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明天的日子,一晃就是三年。常常看着辉月认真的侧面,那时的子霏有种酸楚的甜蜜。等大局底定,等一切动荡都平静之后,他会和辉月说个明白。为什么跟着他跳下湖,那长长的,两个人无助的,象孩子一样,互相舔着伤口,相依为伴的日子。隐龙那么的甜蜜的生活。也有疑问,为什么辉月可以离开的那样决绝。还怪他么?还是因为他已经预知了帝都将有的变乱?新伤迭叠上旧伤,新愁漫过了旧恨。最后奔雷殒命,克伽伏诛,天界元气大伤,风云巨变。辉月是众望所归的天帝,再无人有二言。子霏的伤势始终反反复复难愈,汗青试了多少方法也不能令他好转。子霏自己心知肚明,只要回到隐龙,那里的泉池,白江,可以治愈一切沉疴。但是辉月在这里。所以子霏连一次也没动过想要回去的念头。只是辉月事忙,子霏怎么约见,都见不到。一次,两次。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最后耐性耗尽,硬闯正殿。被侍卫缴了剑押住,他不管,也顾不得反抗,大声呼唤辉月的名字。“辉月!”“我有话要和你说!”“辉月不要走,我有话要说!”“辉月!”“辉月!”辉月恍如不见,恍如不闻。用他独有的淡漠和遥远的目光,隔着一丛丛的屏障,冷冷看着。那眼底什么也没有。没有从前的温柔,没有曾经的天真,没有热恋的纯稚,没有共患难时的肯定信任。被人拖走,茫茫然的忘了反抗。抱着膝待在帝都的囚牢里。那时候犹有心情嘲弄自己。改朝换代,一代江山换帝君。可是这囚牢还是旧时样,一成不变。倒比帝宫大殿上那张白玉椅子还显得稳固。越想越好笑,辉月升基一月有余,称得上事事宽厚。想不到他天帝的囚牢里,面具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许是被行云追打的时候遗在小屋里面。太阳慢慢升了起来,晨雾渐渐变淡不见。痛楚终于平复,子霏慢慢站起来,然后,拖着步子向回走。来的时候轻快,回去的时候却用了足足的半天。到了帝宫的时候,天已经过午了。小侍急得团团转,看到他回去,真喜出望外。子霏只是一径地摇头,不想喝水,也不想吃东西。很累。这个早就千疮百孔的身体,好象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小侍守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子霏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了开来:“现在的天医院……谁当值?如果是文先生或是汉青,请他们中的哪一个过来都好,”顿了顿,喘了几口气:“请司礼官替我转达天帝陛下,旧伤发作,我须得尽快回转,请他安排一下。”小侍答应了一声跑了。子霏瘫在床榻上,四肢沉得象灌满了铅……又象是抽掉了骨头。软软的,沉重的,没有生命力的腐肉一样。可能是病痛的关系,回想起过往。子霏觉得自己早已苍老,因为总是缅怀着过去。却不希冀将来。辉月许是被两百年,他的狂执吓坏了吧。所以这一次总是避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