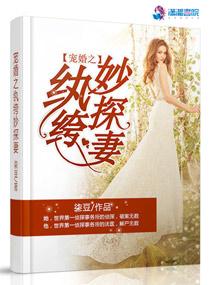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花间一壶酒的全诗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左含章皱眉看着前线奏报,虽然百夷内乱,但如今士气不减,调度有条不紊,只是人数略有削减,对方帐中显然有高手坐镇,军法谙熟,调兵遣将已有大将之风,这一场仗显然会是一场硬仗。
门外牙将忽然来报:“将、将军!”
“何事如此匆匆?”
“门外有人求见,自称是百夷来使和谈。”
“百夷来使?”左含章沉吟片刻:“他们来了多少人?”
牙将颇为尴尬道:“只有一人,带了一大口箱子。”
“只有一人一口箱子?”左含章冷哼一声:“也未免太不把我大齐放在眼中了,叫诸将军来主帐商议此事。至于来使,舟车劳顿,安排他先休息一下吧。”
牙将明白了他的意思,道了声“是”便下去安排了。
在偏帐里坐了大约两个时辰,安排他待在这里的牙将才姗姗来迟道:“使者久等了,将军想见您。”
那百夷使者抬了眼淡淡道:“咳咳……有劳引路。”牙将在前面引路,心想他齐国话说得这么好,难怪被选来做使者。只是看样子身体不大好,脸色青苍,咳嗽得厉害。
牙将在主帐前停下脚步,中气十足道:“禀告将军,百夷使臣到。”
“请进来!”
这声音耳熟的很,崔酒一听便知道是左央左含章。他微微一笑,掀帘入内,朗声道:“左将军,别来无恙啊。”
左央看见眼前人登时愣住了,崔酒穿了一身绣百花的蜡染蓝衣,那袍子是百夷制式,略短,露出他大半截嶙峋的脚踝来。他颈上、手腕、脚腕都缀满百夷风格流苏银饰,走起路来“簌啦啦”地摇曳生姿。六年未见,他看起来消瘦不少,脸颊微微凹陷下去,裸露在外的手腕与脚踝上半点肉都没有,肤色虽受着百夷灼热的阳光,却比当年更显青苍。他腰间佩着的玉符,赫然是代表齐朝使臣身份的青玉符。
“崔酒?”左央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你没死?”
“然也。”
左央微微冷了神色:“你如今是百夷使臣?”
“非也。”崔酒笑道:“我乃上钦点的齐朝使臣,既然尚未有废止的上谕,酒如今便仍是正三品赐银兔符的使臣,全权处理百夷之务。”
“可你如今装扮……”
崔酒缓缓抚过腰间的玉符:“倏忽六年,玉符犹在,衣冠不存。我给将军带了厚礼来,将军派人呈上来吧。”
左央应了,便看见两名将士颇为费力地搬来一个硕大的箱子放在地上,崔酒挥开两位士兵,亲自上前弯腰打开了箱子,里面放着不少旧衣、血书还有些石头、泥板和草纸。
“凤翼三年,酒携五十三人出使百夷,不料左将军自有谋划,偷袭荷郓城不成,使团全部被困百夷,六年被囚,不得回乡。和谈大计毁于一旦,摆流城沦陷,城中三万平民被屠!”他眼神冷厉:“左央左将军,自以为是,欺上瞒下,肆意妄为,你好大胆子!”
左央微微一抖,何止如此,他偷袭荷郓城不成,反致摆流城沦陷,六千守军被坑杀,三万平民被屠。沱县危急,他父亲左炎力守不退,鏖战身死,他临危受命,接手南疆,手下折损过半,只得背水一战。直到梁州驰援,才勉强守住了沱县。此后三年,南疆守军都无力与百夷正面抗衡。
一旁的副将见崔酒来势汹汹,匆忙插嘴道:“当年左将军誓死不降,带兵死守沱县,上谕命其将功折罪,在南疆戍守,无诏不得回京。”
崔酒冷笑:“可左将军戍守南疆六年可有寸功?”
众人默然不语。
“也罢,今日我也不为追究而来。毕竟左将军乃是天子心腹,南疆刀兵,崔某哪里有资格处置?”崔酒目光如刀,在每个人身上剜过,直到众人纷纷低头,无人敢直视他之后,他才翻开册子:“使团当日被困凤流城,宁死不降,被逐至野林,无衣无食,十二人死于水土不服而无医药,两人葬身虎口尸骨无存,七人死于中毒。四年后,百夷改制,我等沦为苦役,十三人不堪劳役,短折而死。使团五十四人仅存二十人,死者衣冠遗物皆在此,生者虽困苦不堪仍心系故国故乡,虽无纸笔却也想方设法写下家书,也在这箱中。这些东西便交由左将军转交,可有异议?”
左央看着那口扎眼的箱子,声音艰涩道:“央定不负所托。”
崔酒略一点头:“如今百夷内乱将定,如今尚有二十人未归,百夷的条件是,三日内,齐军退守十里,回到沱县。诸位将军觉得如何?”
帐内众人面面相觑,廖副将犹疑着开口:“这……军中之事岂可如儿戏?崔公不便插手吧?”
崔酒冷冷地刮了他一眼:“诸位将军此行有几分把握收复摆流城?”
左央抿紧了唇:“至多六分。”
“今日一战之后,左将军又有几分把握?”
“不到五分。”
“除去退兵之外,左将军可有营救之法?”
“……无。”
崔酒断然道:“既无退敌之计,便听我的。即刻传令,疾退十里,每退一里,百夷将放归两名人质,若未见人,即刻停驻。你们各自能调动的亲兵约有千余,这些人留下跟我走。”
左央看着他觉得太过陌生了些,他印象里的崔酒还是当年那个世家子,爱花爱酒,潇洒温文,不笑的时候唇角也是弯弯的。如今眼前人却眼角眉梢里都是讥讽和冷冽,最愤世嫉俗的人也不过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