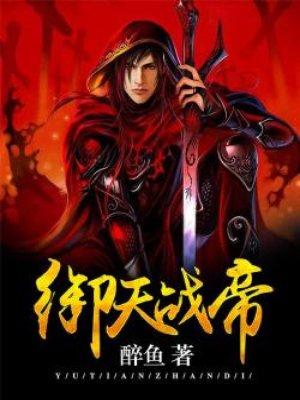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洪荒孤女第3卷 > 第876章(第1页)
第876章(第1页)
幸好雪橇稳住了威尼,不再跌了。一根支杆卡在裂口上,支撑着恰好使母马有时间恢复了平衡。然后它蹄子陷入一块雪中,在厚雪里站稳,踩着了冰岩。乔达拉觉得危险已过,松开雷瑟的缰绳。他一脚踩在冰隙里,提着绳子围腰绕去。
&ldo;拉我一把!&rdo;艾拉一面攥着正在向上爬的威尼的缰绳,一面喊着。
眨眼之间,不可思议的,他瞥见崖边上冒出艾拉的头,一把将她拉了上来。接着出现威尼。它向前拱着身子、攀上裂缝,踩在了水平冰面上。清早的天空抹过一道粉红,紧下面的便是大地,乔达拉长长地舒了口气。
狼一下子蹿了上来,跑向艾拉。一它要跳在她身上,可她觉得彼此都立足未稳,便示意它下去,它就退下了。看看乔达拉,又瞅瞅马匹,它昂起头轻轻地、快活地嗥叫着,然后高声地、久久地唱起它的狼歌。
他们已经攀上一个峭拔的陡坡,并立在平坦的冰面上,但仍未到这座冰山的顶峰。靠冰面边缘是许多裂缝和突立而起的、膨胀的碎冰块。冰面后有一堆突立的碎冰,上面覆满了小山似的白雪。乔达拉越过它们,最终立足在这冰原平平的表面上。威尼紧随其后,蹄下蹦出的块块碎冰又反弹回去,骨碌碌滚着滑在冰岩边缘。乔达拉丫直将绳子死死地拴在腰上,艾拉就踩着他的脚印走。后边是狼在前,威尼在后。
天空已是一片黎明的蓝色。艾拉站在陡坡上回首眺望,不敢回想她是怎样爬上来的。
一道喷薄而出的灿烂阳光映照出一幅难以描绘的图画。在西面,一片平坦无垠,白色眩目的平原在他们面前延伸。平原上的碧空呈现出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蓝色光影。不觉间又融进了红色冰岳反射的蓝绿色光,是一种多么令人销啤的晶莹闪耀的光茫!在遥远的西南方的地平线上,这片碧蓝逐渐变深、变为朦朦胧胧的蓝黑色。
伴着东升的太阳,曾经在黎明前的漆黑天弯上反射着如此灿烂的光焰已经褪淡,而冰冻的水流构成的这片广袤无际、寸土不见的荒原上却是光秃秃;没有树木,没有石头,这貌似坚不可摧的表面上,是那样的庄严沉寂。
艾拉大口大口、急急地唿着气。&ldo;乔达拉,太美啦!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为看到这个,我宁可经受两倍远的旅程,&rdo;她肃然起敬地说。
&ldo;很壮观,&rdo;他说,因为她的反应不禁微笑起来,同她一样不可抑制地感到兴奋。&ldo;但我那时没法对你说。我从前从未目睹过类似的景观,它毕竟不太常见。这里来自上空的暴风雪也堪称一大奇观。趁我们看得清楚,我们还是赶路吧。天气并非看上去那样稳定,而且这明澈的天空和明媚的阳光下,要么是某个裂缝可能会全部裂开,要洛就是悬在头上的某条雪檐坍塌。&rdo;
他们开始穿越冰积的平原,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太阳还不甚高,穿着厚重衣服的他们已汗流夹背。艾拉动手去解自己的带风帽的皮毛大氅。
&ldo;如果你想,你就脱掉它,&rdo;乔达拉说,&ldo;但身上得一直包着点什么。你可能会在这上面被太阳灼伤,还不仅仅是头上呢。太阳一照,冰也能把你烫坏。&rdo;
整个上午,小块的堆积云都在聚合加大。正午时分,它们已汇聚成一大块、一大块的云团。风在下午渐渐加大。差不多在他们决定停下化冰雪取水的时候,艾拉急不可待地又披上了大毛氅。太阳躲进了水汽弥蒙的积雨云中,漫天飞扬、干末样的雪花从浓云里撒下,落在两个行人的身上。冰河同时也在加厚。
33冰川历险
雪愈下愈大,西北风愈刮愈猛,狂风肆虐中夹带着刺入骨髓的凉气,毫不留情地刮在他们身上,他们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在狂风暴雪中挣扎,好似他们不过是空气中一抹淡淡而苍白的水平薄幕。
&ldo;我想我们最好等到雪停,&rdo;乔达拉高声喊道,好让声音超过暴风雪的怒吼。
他们挣扎着支起帐篷,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这无情的狂腌张牙舞爪,好像顷刻间便可将那层御风的皮子从两颗纤弱跳动、誓死要从风雪中闯出一条路的心上扯碎‐他们竟胆敢与这横扫平原、冷酷残暴的暴风雪挑战。
&ldo;我们怎样才能把帐子支好呢?&rdo;艾拉问,&ldo;这天气太糟糕了!&rdo;
&ldo;我记得过去风刮得可不这么凶,不过,我不觉得奇怪。&rdo;
马儿们垂着头乖顺地站着,默默地、顽强地忍受着风雪。狼紧紧地靠在它们一边,用利爪为自己在地上挖出个洞穴。&ldo;也许我们可以叫其中一匹马站到柱子根那儿,踩着不让它离开,一直到我们把它立实。&rdo;艾拉建议道。
他们暂时达成了共识,就是把马匹同时当作帐子的椿柱和支撑点使用。他们在两匹马背上挂起皮帐,接着艾拉好言哄慰威尼站在其中一边上,然后才转身钻进去,心里还祈祷着这母马可别晃得太厉害把帐子抖掉。艾拉和乔达拉蜷成一团,沃夫蜷伏在他们的膝下。他们头上几乎就是马儿的肚皮,屁股底下压着帐篷的另一角。
暴风还不曾平息,天已黑了。他们只好在原地宿营一夜,但先把帐篷重又支稳。清晨,艾拉突然发现离威尼支撑的帐子那边不远,有些乌黑的污渍。她一面惴惴不安地猜测着,大清早便匆匆爬出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