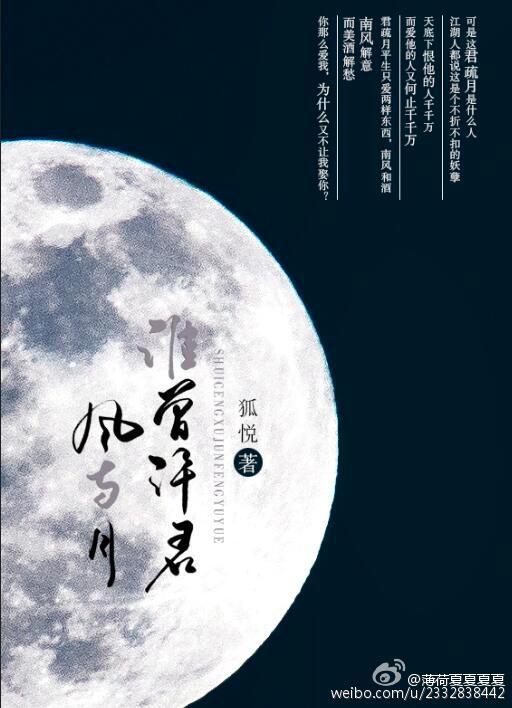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治疗颈肩腰腿疼透骨草图片 > 第 30 章(第1页)
第 30 章(第1页)
说起来奇怪,接下来两天都是这样,菜式天天翻,到后她都弄不明白了,锦和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她打了两次电话找她,都没找到。疑惑之下犯起傻来,跑到水缸里看,心道不会养了只田螺姑娘,天天来给她烧饭吃吧!
田螺姑娘当然是没有,她到隔壁问唐姐,有没有看见上午有到家里来。唐姐头摇得响铃一样,“这两天皮包公司要赶一批货,天天穿珠子穿得头颈都要脱榫了,没有注意呀。”
打听不出头绪只得作罢,她依旧上她班,回来依旧有饭吃。其实她想到了良宴,可是门窗好好,他也进不来。再说他这么傲气,绝不会这种鸡毛蒜皮地方下功夫。也许是寅初?仔细琢磨倒有可能。他不是认得介绍房子中间吗,说不定哪里又弄到了备用钥匙,要想进门来也不难。她忧心起来,这样怎么行呢,真要是他,那挂锁就得换掉了。她一个独身女,房间钥匙男那里,实太不像话了。
这天恰好礼拜天,他说要带嘉树来看她,早上八九点就到了。一大一小两个都穿着西服,站她门前,手里提着茶食和水果。她看到孩子就笑了,那么小,西装笔挺实很好玩。嘉树毫不认生,见她蹲下来,立刻盘着两条小短腿飞奔过来,一下子撞进她怀里,亲热地贴着她脸,叫她“姆妈”。
这一叫倒让大尴尬不已,寅初低声呵斥他,“怎么胡叫呢?爸爸教过,要叫阿姨。”说着讪讪地对她笑,“以前母亲常给他看南葭照片,小孩子分不清,可能错把认作她了,不要生气啊。”
南钦捋捋嘉树头发,他粉嫩脸上亲了一口,“不要紧,孩子还小,慢慢教他,改过来就好了。”说着抱手里到厨房去,问他饿不饿,给他冲藕粉喝。
前后窗都开着,屋子里漾起微微风,吹动了厨房门上半幅碎花布帘,飘飘荡荡,翻翻卷卷。寅初坐沙发里,边上一张香几上摆着她打了一半毛线,灰灰颜色,不像女穿。他展开来看,门幅阔大,应该是给男织吧!是给冯良宴?他心里一沉,转过脸去,装作不经意地问:“工作时间那么紧,还有空打毛线啊?”
南钦把嘉树抱过来,搬了张小竹椅让他坐。大凳子对他来说可以当桌子了,她把藕粉放他面前,让他自己慢慢地吃,抽空答道:“是锦和托给她父亲织,她家里总说她不懂女红,不像个女孩子。她不服气,打算叫代工,到时候好拿回去滥竽充数。”
寅初笑道:“锦和还是这副样子,她父母亲大约不大赞成她做这份工。”
南钦含糊地应了,又道:“早上出去买了菜,今天应当没有什么要紧事吧?这里吃午饭好了。”
他带了嘉树来,就是为了多一些相处时间。留下吃饭当然再好不过了,一起忙进忙出,革命友谊通常工作中产生。
南钦去拿菜篮子,站厨房窗台前愣神。说起那件绒线衫就让她唾弃自己,有一天去百货公司,看见绒线柜台东西不错,也没多想就买了两斤线。回来起了针,织了一晚上才想起来她和良宴已经离婚了,她再也不用操心天冷后他军装里穿什么打底了。自己对着那几绞线哭了一通,哭完了把线都抽掉,后来改了锦和父亲尺寸。
她叹了口气,端起搪瓷盆到外面水龙头上洗菜。听见嘉树叫姆妈,她回过头一看,他正试图跨门槛。寅初从后面赶过来,一把将他抱了手里。
洞开大门里站了一对父子,脸上带着笑,指指点点向她这里张望。南钦突然觉得南葭福薄,如果她耐得住性子,一家三口生活一起,不说看寅初,就是冲着嘉树也能坚持下去。
弄堂里白天是很热闹,哪家来了,有点事,很就皆知了。唐姐是派出来打听消息代表,她脸盆里象征性地放了两双袜子,挨到她边上问,“那个是谁呀?看样子是个有钱嚜!嗳,那个孩子怎么叫姆妈?和冯少帅有孩子啦?”
南钦无奈道:“那个是外甥,今天过来看。”
唐姐一声哦拉得老长,“这么说那位先生是姐夫呀?就说,看样子不像个平常,原来是商会会长!”
这里面物关系别顺嘴都能说出来,实过于显眼,基本没有什么**可言。南钦干干地笑,“唐姐洗袜子啊?好了,让给。”
“不用不用。”唐姐道,“洗,又不着急。中午烧点什么?”
她也不大会做菜,指指盆里鱼说:“红烧鲫鱼。”又指指篮头里,“再炒个菜心。早上买了半只盐水鸭和一盘螺蛳,四菜一汤大概够了。”
“蛮好蛮好,就是炒螺蛳要当心,不能盖锅盖噢,肉太老了吸不出来。”语毕又挨过来一点,拿肩头顶了顶她,往寅初方向努嘴,“看那个姐夫不一般,大概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