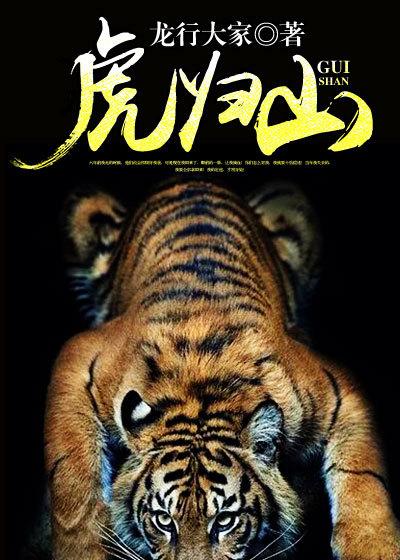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夜航星歌曲完整版 > 第91页(第2页)
第91页(第2页)
“你大晚上发什么神经,跑上来跟我抢被子?”费遐周公开投诉,顿了顿,又补上一句,“刚刚下去倒水了。”
聂瑜叹口气,“那早点睡觉吧,要是还冷记得跟我说。”
随即闭上眼,转了个身,背对着费遐周,自顾自睡去了。
费遐周张了张嘴,反驳的话堵在嗓子眼,终究没说出来。
和费遐周不一样,聂瑜气血旺盛,没过几分钟就把被窝给焐热了,冬夜的寒冷都被阻挡在外。
其实他表面上鲁莽,做事却很周全。他完整地穿着睡衣,长袖长裤,与费遐周之间也隔了不短的空间,只占领了被子的衣角,保持与枕边人的距离,绝不过界。
聂瑜没说晚安,不问他失眠的理由,也不解释自己的行为。但他什么都不用说,一切都已经溢于言表。
小孩,聂哥在呢,安心睡吧。
他总是喜欢用这样熟稔的语气称呼费遐周是小孩,不顾对方蹿高的个头和惊人的智商。不讲理的霸道,和毫无保留的宠溺。
费遐周没有闭眼。
他静静地凝望着枕边人,聂瑜的颈脖线条像连绵的山脉,脖子的后方有一颗小黑痣。
第一次,他任由自己的目光像流水一样倾泻,不设堤防,翻涌滚烫。
他伸出手想要触碰对方,只差几毫米的距离,修长的五指僵在空中,良久,又悄无声息地收了回来。
费遐周紧咬下唇,只觉得鼻尖泛酸。
对于曾经的他而言,黑夜可怕而又漫长,落下的日光是折磨与耻辱到来的预警。
他在无数个寂静的夜里被拖至角落遭受酷刑,他挣扎却无法挣脱,呼救却无人回应。他知道别人是能听见的,无能的痛哭、歇斯底里的呐喊,他们听得到,却装作聋哑,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为他的遭遇献上无用的怜悯。
最可怕的从不是身体上的痛苦,而是被众人选择性的抛弃。
没有人愿意为他的黑夜点亮一盏灯。
他曾经这样以为。
而聂瑜是不一样的。
聂瑜是天生的发光体,是航行在无垠苍穹的发光卫星,每一次的闪烁都是给予他的回应。
第二天的气温有了些许回升。
清早,费遐周有些惆怅。在聂瑜的勒令下,他全副武装,耳罩、手套和雪地靴,从头到脚包裹严密,厚重的毛衣撑起鼓胀的羽绒服,他一身蓝色系的衣服,远远看上去像一颗蓝色的圆球。
然而出门前,聂瑜仍然不满意,扯着费遐周的书包带子将他拽了回来,又绕着他的脖子裹纱布似的缠上了一条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