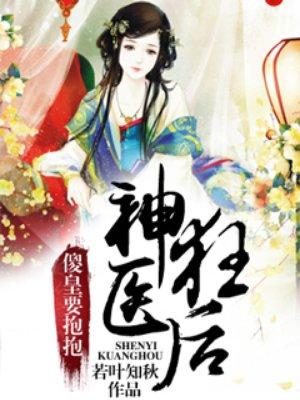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梦溪奇谈免费漫画160 > 第24页(第1页)
第24页(第1页)
“原来大师竟然在市集卖起了猪肉?”“还不止,怀良师傅刻戳子了得,也借着庙产店面,自有一门刻章的生意,也并不与寺内结算。如今已然发了小财,整月也不进寺庙却常去赌坊酒肆,寺庙里长老们都觉得他没有些出家人的体面,都不愿提他,后辈僧人们认识的人自然更少,见到了也只当是寺里的火工杂役。”“原来如此,那怀良师傅现在可在前面集市?”“此间已过午时,食客们都散了,不知道还在不在,也许打酒去了也许听曲儿去了。不过他那铺子还有位学徒的伙计小乙哥。只需找到那面炙猪首的幌子便是了。”“多谢多谢。”沈括喜出望外,赶紧答谢了小和尚转身离开大相国寺,在寺外找到驴,牵着又转回前门集市。故人二月初四午时三刻沈括绕回到大相国寺前门。此时正是午市刚过,夜市未到。大相国寺前门大集市正是客人渐少的闲暇中。只是四周两三楼大店铺外正有棚匠趁着客人稀少搭棚子,敲敲打打让人好生烦躁。沈括仔细观瞧临街铺子上幌子,卖文房四宝、簪花香粉、吃食果子的都各有分野,有朱漆杈子分隔,也有大相国寺派出管理集市的和尚们坐在条凳上或下棋或喝茶,一片安宁景象。这卖吃食的店面中间,又分时令果蔬、现成果子蜜饯和动碳动火的熟食三类。凡售卖类同的都聚在一起,各自招牌幌子也是鲜亮而招摇。当然大相国寺自己产业总是在最显眼位置,远远就可以看到那面相国寺炙猪首的幌子,却见那棚子外靠着炉子的条凳上,躺着一位学徒模样的,似在午睡。沈括过去看到那位正翻来覆去有些烦躁,大概是被附近搭棚子敲敲打打的声音扰了。他见沈括到也麻利起身。“这位可是小乙哥?”沈括作揖道。“正是,客官想要买猪耳还是猪脸?此间没有热的,倒是有几包放冷的。”“不是不是,我想找……”沈括两厢打量,只见铺子里板凳都倒放在桌子上,厨房桌案上摆着几个生猪头,却不见人。“其实,我找怀良师傅。”“师傅沽酒去了。既不买猪耳?可是要刻图章?不如先坐下,等等便来。”小乙麻利起身翻下一条凳子,让沈括坐。沈括便坐下与这伙计攀谈。“刻章倒是也要,但还另有正有事要找怀良师傅。”“我看客观也是文生学子,便知是要刻戳。师傅他片刻便到。若等不及,可先将要刻的章印留下,再留下些许定钱,明日来取便可。师傅阴阳刻法都了得的。”“不不,我还是等等。小乙哥,这附近正店大铺为何还要在欢门外另搭彩楼?”“客人不是本地人,也必然刚进京。”小乙手快,给沈括倒上一杯茶。“正是。前日刚入京城。”“这里搭建的并非彩楼,乃是灯节的彩棚。”“灯节?灯节不是已经过了?”“确实过了,只是上月初八,张娘子薨,这正月花灯会硬生生停了。一些彩棚也只搭建一半,官家仁爱觉得如此百姓便少了上元灯会的乐趣,故而出丧后允诺再办一次,不称元宵灯节,只让百姓们自结灯社、谜社闹一回子。”“这灯节还能补?”“嗨,如今京城里闹……闹帽妖,人心惶惶的,入夜便闭门闭户,酒肆瓦舍冷清的很。朝廷大概也担心出丧后也未必街市繁荣,可知这东京酒税大宗,都是夜市买卖,故而才有此策。”“哦,原来如此。”沈括恍然大悟般喝了口茶,“看来,帽妖一案也苦了民生。”“谁说不是呢……哎,怀良师傅说了,末法之时,多出妖孽,只盼着能冲冲喜,但愿这帽妖来的也突兀,去的也突然。”“小乙哥,如今这京城的人可曾真的恐惧帽妖?”“白天多半是不怕的吧?我看泼皮闲汉们街头巷议凡说到这些,也多有些眉飞色舞,聊的唾沫星子横飞,都说夜里撞见了也不怕;只是这夜间街上却也不甚兴旺,远不似以往那么繁华了。”“哦,哦……”“客人快看,怀良师傅来了。”小乙抬手指去,沈括转头望去,却见二十步外,一名高大发福的中年和尚正拎着一个葫芦,脚步晃荡走来。看面容胡子拉渣油光可鉴的。沈括暗忖:“这便是当年玉树临风的高僧怀丙?”但是眉眼之间却又几分像,也是出众的身高。只是那眸子不再有那分神采而身形也胖大不少。沈括起身想要快步去迎,却又有些犹豫。正在此时,官府净街的锣声响起。锣声响过,却见集市外几十匹高头大马缓缓过来,马上骑士都带着弓箭腰刀好不威风。大相国寺山门旁皂衣护卫纷纷下台阶两厢拱手迎接。马队后面有四人举着回避牌,再后面是一顶四人抬的轿子,这顶轿子倒不甚出奇。只是仪仗有些出格,轿子后面又是紧跟的马队。沈括也见过大官出行,气派大的也有,但是有骑兵护卫害带着马刀弓箭的没有。他心想,如此大排场必然是枢密使狄青大人回“府”了,狄青乃是边将出生,出行自然不是衙役开道,自得有些武将的气派。他稍一转脸看到咫尺外怀良和尚,却见他方才还有些醉眼朦胧,此刻眉宇凝起,恶狠狠盯着那轿子到府门口,众护卫将轿子围的水泄不通,看不到什么了。片刻后,这邋遢肥胖的中年和尚转过头来,凌厉眼神已失,已然恢复平和与慵懒。这才不期看到沈括。两人只对视片刻,都观察到对方神情微微变化。这胖大和尚显然不是寻常人,他似乎已经从记忆深处找到了什么。“怀丙师傅。”沈括双掌合十道。“哈,你便是当年那……”他走过来有仔细打量沈括,“那打破砂锅追问到底的小童?”他已然认出了沈括,这是何等骇人的记忆力,当时沈括不过十岁,相隔十四年,外形上自然相差极大。“正是。学生公务进京,便想着拜见老师,求解十四年前木塔上双球坠地之问。”怀良和尚大喜过望,抓住沈括手臂往铺子里带:“先坐先坐,小乙,切一盘肉来,我与这小哥有大缘分,得喝两杯。”“大师傅,只有冷猪肉了。”“聒噪什么,先切一盘来。再去隔壁赖婆婆那里取些时令果蔬按酒。”“好嘞。”两人就在这铺子里坐下。大和尚将酒葫芦打开先倒了一杯给沈括。“怀丙师傅好记性,还能记得我。”“少年成长,外貌自然变化极大,然而神色却少变。我虽不是过目不忘,记人却极分明。”和尚说着自斟自饮连喝了两杯。“大师傅……”“你问我当年木塔上的疑问?我便只能告诉你,凡重物下落,不论鸿毛或铁锤皆同速。”“轻重同速?”“此事先不细论。我还有些事情要问你。我记得当时你自报家门乃是世家子,若没记错是……钱塘沈家,当时父亲知明州府而入京述职,便暂住在世交的司天监春官杨大人家?”“正是。如今杨大人已然是司天监少卿了。”沈括必须赞叹怀丙这记性。十四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这么说,你今年也该二十四岁。”“正是。”“当初一别时,听你发愿要游历天下?”“确实游历过不少地方。”“这十数年可曾进过京?”“倒是不曾。”“如此说来……”大和尚沉吟片刻,“这次可是为张娘子往生后的京城怪事而来?”沈括不由一怔,不知道这大和尚怎么猜到这些的。“师傅为何这么说?”“呵呵呵……”和尚朗声大笑起来,“我自有些小小神通。”“师傅何必卖关子呢?”沈括急迫问道,他感觉自己又有变成了那个打破砂锅的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