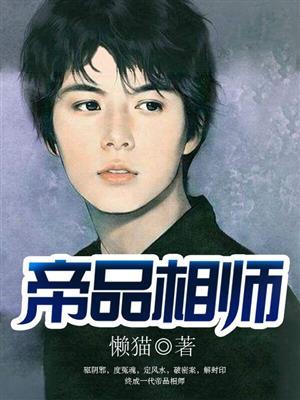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重回高中后和死对头he了 > 第85页(第1页)
第85页(第1页)
他把江麓的袜边也往下褪了点。“崴了这里?”江麓点点头,就见商泊云把背包放了下来,拉开侧链,拿出了一支药油。他把淡金色的药油先在手里揉了几下。“气味有点冲,涂上去还有点儿辣。”和好的那个周末之后,两个人的关系确实已经往前跃了一大步,尽管还差最后一点儿挑明的时机——商泊云想郑重点——但他已经忍不住把“从前”的习惯暴露出来了。某些时刻之后养成的照顾人的习惯。江麓想说自己涂,脚踝已经被商泊云自然而然地握住了。捂热的药油覆了上去,这会儿内疚得不行的商狗子低垂着眼,控制着力道,一圈一圈地揉着江麓的脚踝。还好崴得不算很严重。商泊云闷闷地想。脚踝是凉的,这人的掌心无时无刻都热。对比太明显了,让江麓泛起轻微的异样感。他眼眶疼得发红,压着声音说:“商泊云,你轻点儿。”商泊云的手一顿。过了几秒,他才迟缓地应了一声,继续闷头揉药了。从前总觉得江麓的手好看,弹钢琴的人,骨节修长,腕骨微凸,和手背连成了一条漂亮的弧线,连指甲都是常年保持着圆润的粉色轮廓。脚踝——位置算得上隐秘,可也并非无从得见,譬如二十六岁时的那些夜晚,又譬如现在。这会儿在他手里握着,和春日的削竹似的,绷紧的线条干净漂亮。大拇指忍不住动了下,不轻不重地在踝骨上按了一圈。药油的触感黏腻,贴在两个人的肌肤之间。江麓看着那只握住自己的手,眼睫颤了颤,忍不住出声打断他:“可以了。”商泊云垂眸,很快松开了手。前面的两个人溜了回来。“怎么突然掉队了。”陈彻拂开雾气,气喘吁吁,“我还以为你俩被我的故事吓得跑下山了。”商泊云拿了张纸擦手,顺便把背包递给了陈彻。“我背这个?”“里面一半都是你要吃的。”“那好吧……”陈彻哼哼唧唧,就见商泊云背过身,蹲在了江麓的面前。“江麓,你怎么了?崴到脚了?”陈彻瞪大了眼睛。“嗯,不过我走慢点儿,也可以爬上去。”江麓说。“别逞强。过会儿都要肿得和包子一样了。”商泊云哼笑了声,“再说,我背得动你。”自尊心扑面而来,江麓甚至从商泊云的声音里听出了点跃跃欲试。脚下稍一用力,想走几步试试,痛意锥心,商泊云见此,手向后伸去,把他带了过来。“哎——”江麓没想到他起得这么快,很小地惊呼了声。“我还是有点重量的。”他不得不强调。“嗯嗯嗯。”商泊云声音敷衍,随意把背上的人掂了几下。“估计还要一个半小时到山上,过会儿我们换着背吧?”郝豌在一旁建议。江麓不想再多麻烦人:“我过会儿就自己……”商泊云接话接得斩钉截铁,直接把江麓的话堵了回去:“没事。我一个人就行了。”郝豌若有所思,没再说什么。平心而论,江麓的体型一直偏瘦,这一点商泊云早有认知。二十六岁的江麓也是瘦削的身型,所以他轻易就能够把人打横抱起,然后笑嘻嘻地听那个人轻斥低呼。“抓紧了,这次要是摔下去,我们就真去不了山上了。”商泊云慢悠悠道。江麓却没商泊云那么心安理得,自己再如何也是将近一米八的个子,这么大个人总不是白长的。但商泊云的脾气,有时候有点儿狗倔,江麓转念一想,崴脚确实也有商泊云的责任,遂把手很乖顺地搭在了商泊云的肩上,抱紧了他的脖子。手臂垂在了颈侧,呼吸也变得很近了。准确的说,是江麓的呼吸,就和商泊云的耳朵隔了点距离。商泊云嘴角勾了勾,背着人往山上走。折腾了大半天,太阳终于从雾里照了出来,前面的路变得清晰起来。江麓喜欢晒太阳,身下背上都暖乎乎的,那会儿心惊胆战的感觉也跟着慢慢消失了。“才知道你怕鬼。”商泊云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怕。”江麓说。商泊云来了兴趣:“那是什么时候怕的。不是一般小时候才怕么?你看陈彻,小学还被鬼故事吓得哭,现在就可以讲鬼故事吓你。”“首先,始作俑者是你。”江麓伏在他肩膀上淡声道,“你那会儿是故意吓我的。”商泊云这会儿从懊悔里恢复过来了:“我将功补过?等会儿去了寺里,我在菩萨面前替你求一求,让菩萨保佑你不怕鬼。”江麓拿他没辙,却没忍住弯了弯眼睛。“小时候偷跑去了山上,找不到路。”江麓继续道,“下了很大的雨,风也呼呼地吹,我一个人躲着,动也不敢动,觉得四面八方都是怪物。”“后来夜深了,我终于被人发现了。回来生了次病,做了好几天噩梦。”“你还会偷偷地去山上玩?”商泊云有些好奇,“看不出来啊。”“我也有童年的好不好。”江麓长睫低垂,声音里带了点抱怨。“行。江小朋友,这次的山上没怪物了。”商泊云笑了笑。胸膛贴着这个人的后背,热意和心跳声都清晰,江麓想起很多年前瑟缩在榕谷的山路时淋的雨。没见到妈妈,山路太长,林木太高耸,在风里张牙舞爪。他只记得老纪找到他时打了把红蘑菇似的伞,还有那份被孤独放大的恐惧。做过的噩梦早就忘得干干净净,最后留下了一个怕鬼的毛病。他的手不自觉地蜷缩,选择不再去想以前的事。前面有菩萨,世上没有鬼。“我的脚没那么疼了,过会儿放我下来走吧。”江麓说。商泊云“唔”了声,江麓一听就知道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手臂微微用力一夹,商泊云“嗷”了一声。“我说,过会儿我可以自己走。”江麓一字一顿。“听到了。”商泊云喘出口气来,“刚刚差点没勒死我。”“真的?勒疼你脖子了吗?”江麓低下头去看,恰好对上商泊云侧过的脸。雾气中,许多事物都看不真切,这样的距离里,只有彼此的脸无比清晰,从江麓的角度,能看到这个人的鼻梁有很优越的高度与弧线,要是他愿意,都可以去捏一捏商泊云鼻梁的真假。“骗你的。”商泊云露出笑来,“虽然流氓罪已经废掉了,但也别想着趁机揩我油。”“……”小气鬼商泊云。累死他算了。江麓的手虚虚地搭着,尽量不把脑袋的重量也搁在商泊云的肩膀上。太阳正以缓慢的速度从云雾中显露身形,将要来临的冬天,在满山铺陈的红叶里也不显得冷清,往前几步台阶,陈彻和郝豌偶尔回头,确认后面两个人的步伐。遥遥的,有钟声传来。山巅反而不见如火的枫叶,碧沉的松柏参天,金瓦朱墙的壶山寺披着熠熠的初阳。商泊云扶着江麓踏上最后一级台阶,走走停停大半天,陆陆续续有登山的人超过了他们,这会儿已经过了正午了。壶山寺外已是人来人往,全然没有山间的阒寂。“我小时候来这时,这里就这个样子。”陈彻指着山门外的松柏手舞足蹈,“一点儿也没变。”郝豌摁住了他,很虔诚地对松柏双手合十,陈彻还有点儿懵,无奈胳膊肘拗不过肱二头肌,默默闭上了嘴。“还能再继续走吗?”商泊云后半程尽职尽责地变成了一根拐杖。“可以。我都自己走了这么久了。”江麓看向不远处庑殿飞檐,眼睛亮晶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