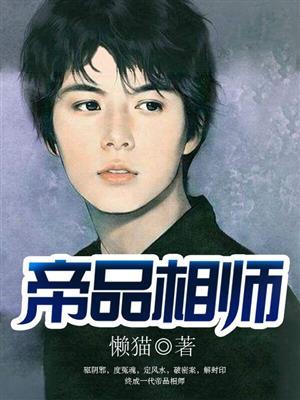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教主,你又变身了+番外 > 第10页(第1页)
第10页(第1页)
那壮汉愣了片刻,忽然惊叫:“你是水行歌!魔教教主水行歌!”喊完这话,就像个神经病一样跑了……水行歌摸了摸下巴,认真的问我:“我脸上有写着魔教教主四个大字吗?”我极仔细的看他,皱眉:“没有。”他的脸上确实没写,但是我们出来时,镇上的大门口非常煞风景的贴了两张画像,一张是我,一张是水行歌。我们两人牵着马站了一会,路上行人纷纷投以探究的视线。“妙手观音龙妙音,盗窃天下财物,生擒者得十万两白银。”“魔教教主水行歌,擅闯唐门禁地,擒拿者得十万两白银。”水行歌看了看,又看我的脸,我摆摆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人不是我。”“那是谁?”我顿了顿,跨上疾风,拉紧缰绳:“唔,大概是我哪个姐姐,或者是妹妹吧。”水行歌似乎明白了:“三生子?”“不……我们是四胞胎。”娘很能生,一胎生了四个,我排不到子时,水行歌就走了。我百无聊赖的对着他的背影挥了挥手,然后拿着棋盘回到自己房里。理好被褥,钻了进去,不管用不用等他回来,还是先美美的睡一觉吧。不知是不是因为知道了龙妙音的事,晚上做了四五个梦都是儿时的。早上醒来,累的头昏眼花,明明睡了那么长时间,却还是精神不振。我拨开床帘,哈欠还没打完,就硬生生咽了下去。屋里有人,是一群人,而且还是一群男人。我裹着床帘,拍了拍脸,一定还在梦里。正摇头摇的起劲,一人沉声:“姑娘这不是在做梦。”“……你们是谁?”“魔教左护法宋毅。”我瞅着为首说话的那人,看着他满脸的胡渣,不禁悲痛,说书的先生明明说魔教两大护法都是超级无敌俊朗的年轻人,而教主才是粗壮大汉。我还憧憬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生之年一定要见见那两个护法,结果少女心又碎了。我忙掩饰下悲痛之色:“你们来这是找你们教主?”宋毅点头:“正是。我们收到风声教主在路上,但是到了这里,却又不见他的踪迹。探得姑娘与教主交好,故擅自进来,还请姑娘不要见谅。”这客套话说的真是圆滑,这几日我跟水行歌确实有点亲近,他们不敢贸然把我拎起来问话也是看在水行歌的面子上,可如果我不识相的说你们真是大胆竟然敢闯进来这种该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丢出去。我笑了笑:“你们教主昨晚说他有事要离开一天,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宋毅和身旁几人面色都是微微一变,没有说什么:“告辞。”见他们十多人离去,我倒是诧异,都说魔教中人生性多疑,怎么这么轻易就相信了我说的话。刚穿上鞋子,就听见一声清脆的鸟鸣伴随着扑翅声飞落房中,我还没来得及跳下床去看,方才走了的那些人又破门而入,宋毅细看驻足在房梁的血鸽,浓眉微蹙:“果然是教主的血鸽子。”我裹好衣服,要是打得过他们我一定会奋起的,可是打不过,只好装包子。一人说道:“血鸽子只听教主之命,从不离身,如今出现在这里,恐怕这位姑娘……”众人神色一凛:“莫非这位姑娘……”我脸一抽,及时摆手:“我跟他才刚认识不久,肯定不是你们的教主夫……”“一定就是教主苦苦寻找多年的那位恩人姑娘吧!”……我又想多了……自从下山后就发现自己越来越自恋了,这是种病,得治。我无奈道:“抱歉,我不是什么恩人姑娘。”宋毅淡声:“姑娘与教主交情必然很深,既然如此,那在此处等候,教主应当还会回来。”我为难道:“我还赶着回去。”宋毅声音更淡:“那就有劳姑娘了。”“……”不要这么不讲道理!被软囚禁的我叫苦不迭,如果人还在五毒山千里之外,倒不比就在山脚下的挂念。就好像一碗肉就在面前你却不能吃。洗脸,有人盯着。吃早饭,有人看着。连蹲个茅厕出来,也看到院子外面围着一圈人。我叹气,以前被正派殴打的时候我常想要是哪天我能威风八面的号令一堆人跟着我一定很拉风,如今确实很拉风,但是未免也太……拉风了……我纳闷的不敢踏出客栈大门半步,出去走一圈回头率百分之百是好玩呢还是游街呢。“水行歌啊水行歌,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趴在桌上戳了戳面前的松软糕饼,“混蛋,哪有丢了手下自己跑出来玩的。”屋内那血鸽从梁子那扑翅,飞落桌上。我歪着脑袋看它,才发现它的眼睛竟然是红色的,爪子如钩锋利非常,一眼看去戾气满满。我正惊叹血鸽果然与普通鸽子不同,血不是白喂的。这鸽子竟然……竟然挪到桌子边缘,然后一屁股坐下了!雪白的尾巴悬空抖着,两条小腿直伸,身子坐的稳稳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