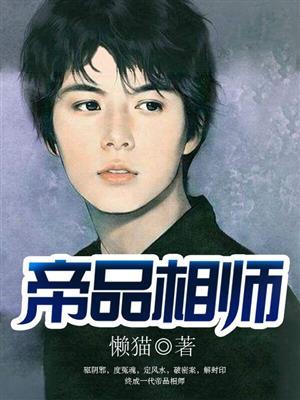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我的金毛空军男友 > 第19章 生病(第1页)
第19章 生病(第1页)
不止舒尔茨一个人,飞行学校全员转移柏林。此一去,舒尔茨只能等闲暇时间返回慕尼黑,但在日益高强度的飞行训练下,他一个月回一次慕尼黑的机会多少有些渺茫。
克林曼想转至柏林上学,为的是与她的莱斯在一起,但莱斯不赞同她这样做,两人为此吵了一架,气头上的克林曼也不给他送行,等列车开走,她才开始后悔。
她去找景澜哭诉,景澜只能做口头上的安慰。
"你这是又何苦呢?"
克林曼哭肿了眼睛:"我只是想陪着他,哪知他不同意,还跟我吵架。"
"莱斯也是为你好。"景澜叹了口气,"你为他放弃在这里的学业,他心里不会过意得去的。"
"那你的舒尔茨呢?你不想过去陪他吗?他没让你去柏林?"
其实,景澜想过去柏林这个问题,但很快打消了这种想法。
她不可能为一个人放弃这儿的学业,即使那个人是舒尔茨。
"他知道我不会那样做,他很尊重我的想法,何况我答应他,我有空的时候会去柏林看他。"并且,他们还约定了书信来往。
慕尼黑和柏林两个地方的信件,应该会很快到达对方的手上。
而且假期过些天就要结束,去柏林几天又回来,时间非常紧促,她和舒尔茨,这段时间只能靠写信来寄托思念。
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克林曼暂时的放下了她的党派宣传,跟景澜哭完的第二天,乘坐火车前往柏林追随莱斯的脚步去了,这也算是跟他求和。
她跟景澜说开学那天回来。景澜才不相信,以她恋爱至上的脑子,铁定开学一周后才回来。
最近流浪的民众日渐增多,食物几乎快要无法供应,景澜在救济处,已经见过几个因为饥饿和寒冷而死的人,这令她对死亡笼罩了一层阴影。
台灯下,景澜看着舒尔茨来信,她压抑的心情才得以缓解。
舒尔茨在信上说,他在柏林一切顺利。除了有些学员太过笨蛋外,还有他也要进行更深层的飞行训练。
他违反了长官的命令,被罚了三天禁闭。这封信是在他禁闭期写的,写完后就托莱斯找人寄回慕尼黑。
"那老头实在是不开窍,他还是坚持继续实行那套早年的空战技术,这太过于落后,飞行需要革新,他还骂我鲁莽。"信上开头是舒尔茨对他长官的控诉,后边是对莱斯的。
他在信上说,克林曼来到柏林后,莱斯一有空就偷偷出去跟她你侬我侬,看的他好生嫉妒。
"你知道吗?看着莱斯和克林曼他们俩难舍难分,我愈发的想念你了,我的甜心宝贝,想念你柔软的唇,你白嫩的手,你乌黑的长发,我想念你的一切。"
"我是多么想在这个寒冷的天气拥抱你,为你渡去温暖,可惜,上帝不给我这个机会。"
看到信上最后一句,景澜忍不住笑了。
"你专一、忠诚的日耳曼金发骑士,在柏林飞行学校一处禁闭室落笔。"后边空白的地方,还画着个人像。
景澜辨认了好久,才模糊看出来一个轮廓,他画技着实一般,但可以确认的是他画的是他自己。
景澜哭笑不得,又把信重新一字一句的看了一遍,然后把它封好,放进抽屉里,动作对其极其的珍护。
这是他给她的第一封来信。
思念的话语早在脑海里整理了一遍,景澜从另一个抽屉拿出全新的信纸,正要提笔落字,控制不住咳嗽起来。
救济处人多混杂,加上天气变化多端,生病的人不在少数,她也被传染了。
信写完,景澜去倒了杯热水,家里的药所剩不多,药物现在也非常稀缺。她觉得只是小咳嗽,喉咙不疼,估计过几天就好了,没必要浪费药。
景澜没把这个小病放在心上。没过几天,她的病越来越重,反复发烧,甚至有高烧的趋势,她把家中最后一颗退烧药吃完,还是不顶用,依然发烧不停。
她意识到自己得去医院了。海伦娜太太的房子早已熄了灯,克林曼还未从柏林回来,她只能强撑着身体独自前去。
一月的慕尼黑与十二月的天气相差无几,甚至更为湿冷,这是一个雨夹雪的夜晚。
景澜拉紧脖子上的围巾,吸了吸鼻子,撑开伞关了门。
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寒风也格外冷冽,她不久前才退的烧,这风扑面而来,脑子又开始一阵晕眩。
她此时无比想念远在柏林的舒尔茨,他要是在的话,他一定立马把自己送去医院,并仔细呵护。
还未出路德维希大街,脑袋发昏的感觉愈发严重,景澜停下脚步,倚靠在路灯柱上。眼睛看不清前方的路,一阵天旋地转,终是撑不住,雨伞从手中跌落,整个人倒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