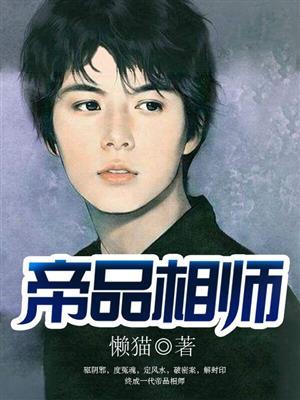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破阵录 > 第二百一十章 争吵(第1页)
第二百一十章 争吵(第1页)
却说那上清宫中,此刻五峰首座齐聚一堂,只是此刻却并无一人开口言说,连那端然正座的辜御清,此刻亦不过轻支额头,若有所思地望着厅堂正中那一盏紫铜香炉,也不知这位名动天下的正道巨擘,此刻心中究竟所思为何。
不多时,只见着一位徐浣尘换了一身崭新衣裳,独自来到大殿门前,拱手道:“弟子徐浣尘,拜见各位长老。”
辜御清点了点头,示意徐浣尘快快入内,上下观瞧了一番这位入室弟子,见着神完气足,早没了半分当日混沌迷惘,这才笑道:“闻听你这几日身子见好了,这才传你过来,今日一看,的确气色恢复不错。”
徐浣尘入殿先行大礼于掌教师尊,再依次拜各位长老首座,这才说道:“承师傅挂怀,弟子当日学艺未精,中了魔道妖术,若非师傅暗中相助,弟子怕是已殒命当场。”
雍少余听罢,心中暗暗思索:“原来当日浣尘能与鱼向晚交手不败,果然便是掌教师兄暗中相助,想来掌教师兄内力浩渺,竟已到了可隔空传功的地步,如此境界,委实是正道之福。”
而辜御清却是浑不在意,似乎徐浣尘所说之事,于他全不放在心上,只是甩了甩衣袖,笑道:“邪魔外道打上山门,莫非我还看着你受了折辱不成?只是可惜了渊狄,同为我宗门翘楚,为师却未能救下他,此乃是我之过,日后定当要去宗门祠堂,向列位掌教先贤赔罪。”辜御清一边说着,心中自是又想起那尚未露面,便横遭杀戮的刘渊狄,话语之间,亦全是哀情悲戚,“田师弟,你齐云峰遭此劫难,却非根基动摇,我看你门下仍有贤良弟子,回头择个吉日,我再亲传他们几手功夫,以略偿损失。”
田烛自当日受了化魂大法钳制之后,与雍少余比拼掌力受了内伤,本需静养数月方能恢复,但毕竟事关本脉弟子亡故,不过几日间,强自运功冲开脉络淤塞之处,竟也行走如常,若非他自身功力深厚,这般行事,已极是艰难,此刻面色虽灰白一片,仍是略略点头,低声说道:“掌教师兄言重了,齐云峰一脉弟子皆受命匡卫正道,若是魔道攻回中原,自然也要奉命斩杀,少不得伤损,渊狄虽身死敌手,但死前亦硬拼相斗,也算尽力了,师兄不需太过自责。”
他此刻本就气力不足,此刻言谈到自家弟子亡故,更是牵动心事,火从心起,越说声调越沉,但话音却隐现急怒之气,当即面色一阵灰白一阵赤红,随即剧烈地咳了起来。
辜御清长叹一声,从袍袖之中掏出一个瓷瓶递了过去,说道:“师弟切莫太过伤心,我今日召集诸位过来,便是要给各位一个交代。”
众人听了,纷纷点头,堂堂正道第一门派,竟在门内比武大较之日,被外敌就此攻入,耀武扬威一番,又扬长而去,虽救下来一众正道高手,但毕竟事事处于被动,的确是颜面太过伤损,众人无不静候这位掌教真人站出来主持大局,而辜御清看得分明,见着田烛将瓷瓶里的药丸吞下一粒,面色渐转恢复,这才继续开口言说。
“今日之会,其实我已思忖颇有时日,自两年前,江湖上有侠义盟之事起,便已深藏于心,只是当时虽已觉察出武林之中略有风波,但却仍念着顺势逐波,不欲强加干涉,只是两年间,江湖之中,宵小渐增,到了如今,魔道竟能破山门而入,实是骇人听闻”辜御清沉声相叙,大殿之中安静得似乎能听到香炉之中静静燃烧香木之声,众人斗清楚得很,辜御清此番话语,几乎决定着未来数年乃至十数年之内,正道武林如何动向。
“当年正道昌隆,魔道遁走,江湖是何等兴盛,但如今,却屡屡受挫于魔道之手,想来便是这正道人才已渐趋凋零,前些时日齐云峰弟子刘渊狄亡故,两年前玄岳峰弟子墨止失踪,都是极可惜的伤损,”辜御清说到此处,也
不自觉地朝着雍少余处望了一望,只见着雍少余在听到“墨止”二字之时,仍轻轻抓紧了衣衫,但面色始终古井无波,全然看不出半分情绪,“故而,依我所见,重启百脉会武,再开正道人才选拔之事,方是当今大事。”
他这话一出,厅上众人无不侧目,原来这百脉会武当年之所以荒废不复,便是因御玄宗弟子沈沐川之故,当年正道虽兴盛无比,但仍需储备新锐人才,扩充武备之选,而沈沐川自然便是那个中翘楚,只是当年沈沐川为人豪傲无羁,处处皆要占个头名,手下快剑无匹,却绝无半分相容相让,一路比拼,却是一路损伤,及至他赢下剑宗魁首之名,已是将当时江湖中用剑新锐伤了一圈,而随后更是一言不吭,便弃了会武总魁首之争,将百脉会武活生生打成了个烂摊子,御玄宗虽身为江湖正道名门,却也极是说不过去,为此,江湖各门各派还曾一同上山门讨要说法,当时便是身为御玄宗大师兄的辜御清站了出来,替自家师弟挡了这一劫难,由此之后,各门各派再不愿将自家人才现于人前,这百脉会武自然也就日渐荒疏无人再提了。
而今日,辜御清忽然再次提气,显然已是无奈之举,任谁都看得出来,这一遭魔道能径直来到御玄宗金阙峰山门之前,便能如此来到江湖任何一门派腹地之中,如此武力,已是不可小觑的地步。
“师傅”
徐浣尘忽然开口,轻轻地喊了一声,辜御清望了望他,却也不恼他此刻插嘴,只是说道:“浣尘有什么想说的?”
徐浣尘剑眉紧蹙,似是仍在心中犹疑,但他与墨止不同,每每开口,必定已是思忖定下,方才发声,此刻也缓缓说道:“师尊所说,弟子认为极是,只是若如此,便认定是魔道所为,怕是还略略欠妥。”
他这话一说,众人更是大皱其眉,三云道人率先怒道:“放肆!尔等小辈,知道什么!这天底下,莫非还有人愿意冒充魔道妖人不成!掌教师兄莫非还识不出魔道之人么!”
徐浣尘说道:“弟子绝无怀疑之意,只是从来便听说,魔道其名之下,仍细分四大门阀,乃是‘血竭堂’、‘异鬼道’、‘苦心禅宗’和‘龟鹤阙’,当初天劫老人便是以血竭堂堂主身份,将四门统一麾下,弟子不才,于瀚海阁中略读了关于魔道四门的古籍记载,其中血竭堂手段最是狠辣霸道,异鬼道则是取鬼道阴灵的修习法门,苦心禅总则是与当今澄音寺相立相对的佛理之争,而龟鹤阙则是主攻炼药炼毒之属,这四门功法大相迥异,却无一门主修那操纵人心之术弟子当日所中那邪术,乃是专攻心智之法,但魔道之中,却无一门有此能耐,故而弟子斗胆猜测,当今江湖之中,或许存有别股势力,打着所谓魔道幌子,煽动矛盾,以策骚乱。”
三云道人双眉倒竖,怒喝道:“区区小辈,那瀚海阁古籍,莫非只有你读过不成!百年前所载所记,今日如何能算得数?若是妖人于百年之间又生出古怪心思,创了这一门功法,莫非我们还要听你所言,置若罔闻不成?”
徐浣尘拱手俯身,但话语却是愈发坚定:“弟子不敢放任,更不敢置若罔闻,从来修道所为,便是匡扶正道,无论这股势力究竟是魔道,还是其他门派,皆绝非善类,弟子只是认为,不可就此便断定一切皆是魔道所为。”
三云道人尚未说话,只听得灵武峰首座谷道梁率先冷笑几声,说道:“嘿嘿,想来是当年卢龙关一战之后,咱们的徐大弟子,如今是对魔道生了怜悯敬仰之心了!”
当年卢龙关一战,世人只知萧家军马奋战退敌,御玄宗和一众江湖帮派于其间鼎力相帮,故此才有保家卫国一胜之力,但却无人知晓,这所谓的御玄宗鼎力奋战,实则不过是徐浣尘与墨止二人而已,至于那一众江湖帮派势力,便是当时
由孙青岩所率的魔道部曲集中相助之功。
徐浣尘脸色猛地一白,立马说道:“弟子岂敢!只是以古籍推论”
谷道梁冷哼道:“什么古籍推论!如今魔道猖獗,祸及天下,你却跟我们说什么不可妄加论断,若非魔道挑衅,你倒说说,是何人与我宗门为敌?依我看呐,嘿嘿,你与那个墨止,都是在西北着了魔教妖人的道儿了!那墨止想必也是奔着魔道而去了,毕竟当年沈沐川”
他话未说完,雍少余已是勃然而怒,霍然起身,厉声喝道:“谷道梁,你说便说,何必牵连我那老七弟子!莫非你灵武峰门下没个提得起个儿的,便要诋毁别脉弟子不成!”
谷道梁斜眼瞟了一下,又道:“据说那个墨止入门之前,便与沈沐川和魔道凶星青辰撇不干净,谁知道他究竟是打着什么心思上山”
雍少余听在耳中,更是怒不可遏,正要开口,却见徐浣尘率先说道:“谷师叔这话说得实是不妥,墨师弟自与我下山后,事事皆办得妥当,西北夔陵村一众村民百十口性命得以留存,全赖墨师弟孤身入侠义盟为饵,方才事有转圜,师叔既不曾随我们一道前去,如何竟能这般以恶度人!”
“砰!”
只见着谷道梁脸色一红,重掌便在桌上拍了下去,他掌力何等深厚,当即便将那一张紫檀硬木桌拍得粉碎:“区区小辈,莫非还要教训我不成?”
“教训谁?”
辜御清忽然沉声开口,众人此刻虽各自争吵,纷乱不堪,但辜御清却一声沉喝,将众人话语尽皆压了下来,即便是素日里威严赫赫的首座长老,也不由得各自按下怒气,不敢再多说半句,只有徐浣尘粗粗地喘着气,双肩不住地上下抖动,显然是动了怒意。
“浣尘,你也太放肆了。”辜御清的话语,沉厚至极,缓缓地传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