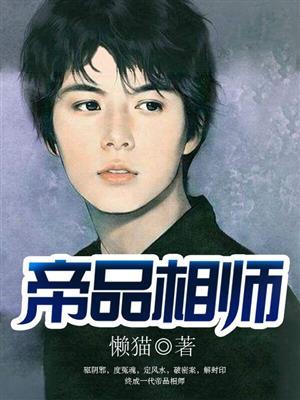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校园适合养的狗 > 白墙(第1页)
白墙(第1页)
许眠欢最后的记忆是她在轧轧的车轮声和清浅的松柏香里睡去,第二天她睁开眼,在宋溺言的家里醒来。
她抬起眼睫,漫眼全是白,就连暗角都被这惨烈的苍白堆砌,白是最纯粹的颜色,华贵绮丽也许庸俗,可当这荒芜的白囚禁一切,许眠欢觉着还不如俗气的华美,这样干枯的空洞太孤独,太森然,甚至还有些残忍。
许眠欢漫无目的地瞎想一阵后就敛回神思,她惺忪着睡眼,坐起身来,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不着寸缕,胴体上缀满暧昧的印痕,她苦恼地红了侧颊,挪动着臀部勾了几件宋溺言来穿。
勉勉强强把一身吻痕藏在松垮的衣服里后,许眠欢踩下床,险些直接摔倒在地,脚尖点上地板时她才惊觉自己的双腿仍然软得跟滩水似的,许眠欢连忙抓住床头,这才勉强站稳。
她在心底直骂宋溺言禽兽,扶着同样是白色的床头缓了好一阵,才试探着慢慢挪往房门的方向。
打开房门又是漫眼的刺白,许眠欢不适地揉揉眼皮,扶着墙拖着步子继续往前挪。
为了从他的家里偷溜出去,许眠欢踮着脚尖,竭尽全力不发出一点声音,穿过长长的走廓,许眠欢踩入客厅,她顺便瞥了眼挂钟,居然已经下午一点。
!下午一点!许眠欢登时欲哭无泪地苦下脸,难怪她没有看到宋溺言,敢情他早就去学校了,这下可好,她直接喜提人生中第一次旷课。
许眠欢就抱着这样颓丧的想法抵达玄关处,她弯下腰,捞来自己那双帆布鞋,那脏兮兮的鞋面和宋溺言一双双一尘不染的运动鞋摆在一起,真是对比惨烈。
反正都是要被人故意踩脏的,不如让它一直脏下去,最起码那些人会嫌弃到不愿意再去用力碾她的脚趾。
许眠欢恍惚着,蹲下身系鞋带,过长的衬衫下摆点水般轻搔着地毯,就在这时,她的肩膀突然被人紧紧攥住。
毫无预兆的动作差点拍飞她的魂,尖叫当即冲破唇齿的桎梏,许眠欢咽下吊在嗓眼的心脏,惊魂未定地回过眼,看清楚身后少年的精致面容后,更加惊魂未定起来。
他微微垂着桃花眼,平静地问她:“你要去哪里。”
许眠欢从前以为自己最害怕的是宋溺言笑起来,可现在她才惊觉,他这样无波无澜的平静,她也很是害怕,许眠欢的唇皮都开始发抖,她不敢看他的眼睛,只嗫嚅着小声回答他:
“今天,今天是周叁,我要去上课。”
让许眠欢心惊胆战的,是事到如今她实在拿不准他的想法,她不能从他的动作里猜到他的态度,不能从他的字句里揣摩他的情绪,这样的未知是一种慢性酷刑,她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绞刑架还是沸水。
或者还有第叁种可能。
第叁种可能是宋溺言扯着她的头发,逼她站起身,将她的头按在那冷漠的白墙上,扯碎她的下裤,硬生生将晨勃的肉棒刺进去。
第叁种可能是逃离近在咫尺,她的灵魂却被坚硬的性器钉牢在情欲里。
少年的手指探进上衣揉她的乳,他状作随意地一记深顶,就足以顶碎她勉强张贴的端庄。
他在她耳边嗤道:“湿得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