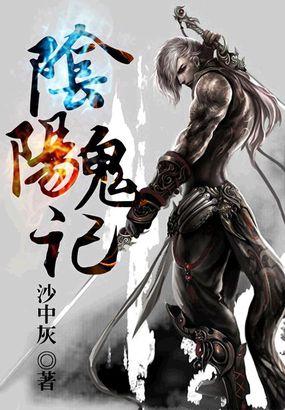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被迫嫁给仇敌之后gl山楂 > 第37页(第1页)
第37页(第1页)
奚清川见状,顿觉荒谬绝伦。今夜乃是他与宁嘉徵的洞房花烛夜,适才他正逼着宁嘉徵为他口淫。未曾想,平白无故地被一穷奇搅了局,他的娘子甚至还抚摸起了穷奇来。穷奇呆滞着被少年摸了好几下,才张口道:“吾可是会吃人的。”“好呀,我把自己给你吃。”宁嘉徵笑意盈盈,一指奚清川,“劳烦你顺便将他一道吃了可好?”尽管宁嘉徵正指着他的鼻子,撺掇着穷奇将他生吞,但奚清川从未见过宁嘉徵这般笑过,不禁有些失神。所幸他并非色迷心窍之徒,即刻回过了神来。他不愿坐以待毙,正欲发难,突地听闻穷奇道:“吾现下不饿。”宁嘉徵无不遗憾地道:“那便待你饿了再吃吧。”穷奇不曾见过如同少年一般迫不及待地被他拆骨入腹之人,直觉得少年更加特别了。他已然上万岁了,却未尝与人或是兽交过尾,时常被父亲催促。父亲担心他孤家寡人,有朝一日会自闭,而他不是搪塞父亲自己爱清净,便是坚称要先除了魔尊兰猗,否则无心于情爱之事。而此刻,他突发奇想地以硕大的爪子挑起少年的下颌,问道:“你可愿委身于吾?”他不通凡人所谓的道德伦理,压根不认为在洞房之中,当着其夫的面,向其求欢有何不妥。奚清川登时怒不可遏,他贵为正道魁首,这凭空出现的穷奇不但扰了他的春宵,竟然还胆大包天地当着他的面,调戏他名正言顺的娘子,乃至于向其求欢!下一息,乍起的掌风挟裹着千年的修为蹭过宁嘉徵的鬓发,直逼穷奇。宁嘉徵下意识地旋过身去,护住了穷奇。穷奇抬起爪子,轻轻一挥,这掌风便消弭了。掌风狠厉,却连穷奇的毛发都未能拂动,更遑论是伤及穷奇的皮肉了。宁嘉徵长舒了一口气,显而易见,这穷奇倘使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他便能摆脱奚清川的禁锢,亦能救出娘亲、小妹以及“王不留行”,甚至还能将奚清川千刀万剐,以报仇雪恨。穷奇摸了摸少年被掌风斩断的那缕鬓发,不解地道:“你不过是肉体凡胎,何故挡在吾面前?”“因为我领教过奚清川的厉害,唯恐你有所不测,你可是第一头不怕我,愿意被我碰触的毛茸茸呢,亦是因为我见不得奚清川伤及无辜。”宁嘉徵自嘲道,“是我太不自量力了,诚如你所言,我不过是肉体凡胎。”穷奇摇了摇大脑袋:“吾喜欢你保护吾。”他天生便是凶兽,他若愿意,只消一口气,便能吞下整整一城池的百姓。故而,即使他嗷嗷待哺之时,都无需保护。这是他第一次被保护,被一较他弱小良多的凡人保护的滋味居然不差。宁嘉徵眉开眼笑地道:“当真?”穷奇回道:“当真。”宁嘉徵自小被爹娘教导长大后要锄强扶弱,虽然他没能锄得了强,穷奇亦不弱,但穷奇所言仍是教他心生欢喜。奚清川大吃一惊,心道:决计是这穷奇走了狗屎运,才好命地挡住了本宗主这一掌。穷奇对须臾前使出了雕虫小技的修士视若无睹,只望住了少年,再度问道:“你可愿委身于吾?”宁嘉徵料想穷奇误会了,遂解释道:“我固然身着嫁衣,面涂脂粉,但我并非女子。”“吾一眼便看出了你并非女子。”穷奇咧开嘴巴,权当露出了笑来,“无妨,吾男女不忌。”于奚清川而言,这穷奇张着血盆大口,能轻而易举地将宁嘉徵囫囵吞下。于宁嘉徵而言,穷奇笑得人畜无害,穷奇爪子上的肉垫更是弹性十足,居然还是粉粉嫩嫩的颜色。这穷奇明明是凶兽,粉粉嫩嫩的肉垫未免有损于穷奇作为凶兽的威严,但颇为合他的心意。不久前,被这肉垫抵着下颌的感觉过于美好了,恍若正置身于一场美梦。少时,他好容易将自己从“终于有毛茸茸愿意同我亲近”的美妙中拉扯了出来,继而毅然决然地道:“你助我澄清真相,还爹爹清白,使奚清川身败名裂,我便委身于你。”现如今,奚清川与穷奇皆是刀俎,而他却是鱼肉,他必须二择其一。相较于作恶多端的奚清川,他当然更愿意委身于穷奇。纵然穷奇全无人样,好在穷奇手感上佳,只是皮毛比“王不留行”粗糙些。况且在所谓的洞房花烛夜,将初夜献予穷奇,能使奚清川尊严扫地。穷奇不知少年与其口中的奚清川有何过节,并不细问:“可,只这好处吾得先尝尝。”宁嘉徵深吸了一口气,冲着穷奇笑道:“悉听尊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