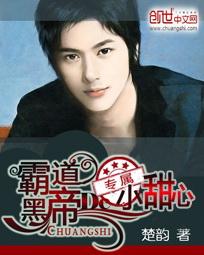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哑巴全文免费阅读答案 > 第42章 桃花扇(第1页)
第42章 桃花扇(第1页)
没想到一转眼,你已经跟了我快七年了,”白承恩拨了一下茶盖,把茶水掩起来,“我还记得你的声音,像黄莺一样,不夸张。”
苏狸缩了一下脖子,心底的苦楚犹如一根藤曼不断缠绕。
“现在还对戏曲感兴趣吗?”
苏狸摇头。
——没有了。
白承恩哀声叹了口气:“真是天妒英才,这么一个好嗓音,被老天爷收了去。”
“我还记得你最爱唱昆曲的《桃花扇》,”忽地,白承恩压低腔,转嗓,随口唱了一句,“‘娼家从良,原是好事,况且嫁与田府,不少吃穿,香君既没造化,你倒替他享受去罢。’”
苏狸低头不语,默不作声。
“如何?”
苏狸抬眼,微笑表示称赞。
“守楼一回,你唱得最好,你师母尤其爱。”
白承恩老了,眼睛笑的弯起来,“明末政局动荡,党政斗争尖锐,侯方域出身商丘侯氏,侯家历代显赫,侯大将军手握兵马。李香君在秦淮河上媚香楼妓院陪客饮宴,对于侯方域别有用心的梳笼,她一见倾心。”
苏狸放在身前的两只手,扭捏了一下。
她静静听,“这固然起于青春年少的儿女私情,但也是出于李香君对复社文人的倾慕。李香君师从苏昆生学唱戏,温柔纤小,宛转娇羞,但性格早熟,漂亮聪明,新婚燕尔之际,她向杨龙友提出了妆奁一事。”
苏狸记得这里。
她眸光微闪,脑中自然而然浮现了那句话——“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却也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在奴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问个明白,以便图报。”
白承恩说的口干,重新端茶,细抿了一口。
又继续说:“狸儿,李香君像你,不甘受人恩惠,不甘寄人篱下。”
一样的固执,死板,执拗,却走上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命运。
白承恩虽欣赏李香君,但却害怕苏狸成为李香君。
“你那个工作还在干吗?”
苏狸哆嗦了一下,如实回答:
——没有了。
“那就好。”
白承恩松了一口气,好好的姑娘,不能真陷在那了,毕竟知黑守白,可不是件易事。
“老师这边有两份差事交给你。”
苏狸呼吸一滞,不知是因为李香君,还是侯方域,她竟有些紧张。
“一个是来自我,一个是来自你师母。”
手心黏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