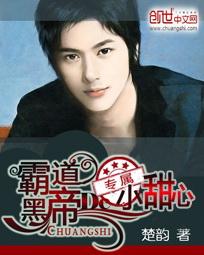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重庆最大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我们的警力在许多方面还是挺优秀的,就凭这些蛛丝马迹,他们追踪到了这个女孩,确认她的身份——名叫多萝西·埃文斯。她被控谋杀。警方警告她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将被当作呈堂证供,但是她坚持发表辩护声明,又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详细复述了一遍,没任何新东西。
“她是这样说的:她是个打字员,一天晚上在电影院和一位衣着入时的先生结识,那个人说喜欢她。他告诉她,他名叫安东尼,建议她来自己的太阳谷别墅看看。她当时并不知道他有妻子。他俩约定接下来的那个周三她去太阳谷——就是那个特殊的日子,你该记得,那天仆人去了伦敦,而他的妻子也不在。最后,他告诉她他的全名是安东尼·塞斯尔,同时说了他房子的名字。
“她如约在那个晚上来到别墅,见到了塞斯尔,他刚从球场回来。尽管他承认自己很高兴见到她,但这个女孩却说一见面他的态度就有些奇怪。一般隐约的恐怖感涌上心头,她真希望自己没有来过。
“一顿简单的晚餐后——晚餐是早就备好的——塞斯尔提议出去走走。这个女孩同意了,他带她走出房子,不久,他们沿着那条‘羊肠小道’走到高尔夫球场的跑道上。然后突然间,正当他们经过第七个球座时,他似乎完全丧失了理智,从口袋中掏出一把手枪,挥舞着说他活到头了。
“一切都完了!我被毁掉了——完蛋了。你应该和我一起走。我先杀了你——然后是我自己。他们明天早晨会发现我们的尸体紧挨在一起——一起赴了黄泉。
“等等——说了很多这一类的话。他抓住多萝西·埃文丝的胳膊,而她,此刻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对付眼前这个疯子,于是疯狂挣扎摆脱他的控制,失败后又去抢夺他手里的枪。他们撕扯在一块,挣扎中他一定扯下了她的头发,扣子上缠住了她外套的纤维。
“最终,经过殊死搏斗,她挣脱出来,穿过高尔夫球场逃命,时刻担心会被子弹击倒。她被矮树桩绊倒了两次,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去火车站的路,发现并没有人追上来。
“这是多萝西·埃文斯的故事版本——她一直都坚持这个说法。她矢口否认自己曾用帽针袭击他——尽管在那种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自卫行为——而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在尸体附近的金雀丛中,的确找到一把左轮手枪,这和她的说法相符,而这把枪没有开过火。
“多萝西·埃文斯被送去审判,但是案情仍然是个谜。如果她的说法可信,那是谁刺中了塞斯尔上尉?另一个女人,那位棕色衣服的高个儿女人,她的出现似乎给他带来极大烦恼。至今没有人解释过她和这个案子的联系。她似乎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高尔夫球场的人行道上,然后从那条小道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再听说过她。她是谁?当地人?从伦敦来的?如果来自伦敦,她是坐汽车还是乘火车来的?除了身高,她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似乎没有人能描述她的外貌。她不会是多萝西·埃文斯,因为多萝西·埃文斯娇小白皙,并且那时已经到火车站了。”
“他的太太?”塔彭丝提议,“会不会是他的太太?”
“很合理的提议。但是塞斯尔太太也是一个小个子女人,并且,哈拉比先生一眼就能认出她,似乎她确实不在家。案子的另一个进展渐渐明朗。波派库恩保险公司正在进行停业清算,账目结果表明大量资金被侵吞。塞斯尔上尉对多萝西·埃文斯说的那些疯话的原因现在已昭然若揭。过去这几年他一定有计划、有步骤地贪污了大量公款。哈拉比父子都不知道这些事。他们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案情就是这样。塞斯尔上尉处于罪行败露和破产的边缘。自杀是最自然的解决方式,但是致他死亡的伤口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谁杀了他?是多萝西·埃文斯?还是那个神秘的棕衣女人?”
汤米住了口,喝了一小口牛奶,苦了下脸,接着小心地咬了一口奶油蛋糕。
2
“当然喽,”汤米小声说,“我立刻就发现这个特殊案件的关键所在,就是在那儿警察误入了歧途。”
“是吗?”塔彭丝急切地说。
汤米烦恼地摇摇头。
“但愿我的看法是对的,塔彭丝,这对于坐在‘桌子上首的老板’来说,发现某个关键环节易如反掌,倒是这个结局难倒了我。是谁杀了那个家伙?我不知道。”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好几张剪报。
“还有——这些是最新的照片——哈拉比先生,他儿子,塞斯尔太太,多萝西·埃文斯。”
塔彭丝忽然抓起最后一张,仔细端详了一会儿。
“她没有杀他,”她最后说,“也根本没用帽针。”
“为什么那么肯定?”
“女人的直觉。她是短发。现在二十个女人里只会有一个用帽针,无论——长发或短发。现在的帽子都能扣紧——没必要戴这个东西。”
“但是她仍有可能随身带着一个啊。”
“我亲爱的孩子,我们可不像收藏传家宝一样藏这些东西!她带着个帽针来太阳谷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一定就是另外一个女人干的,那个棕衣女人。”
“但愿她不是那么高。那么就有可能是他的妻子。很可疑,她们总是关键时刻不在场,因此就没有作案嫌疑。如果她发现她的丈夫和那个女孩调情,那她带着帽针去找他算账就十分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