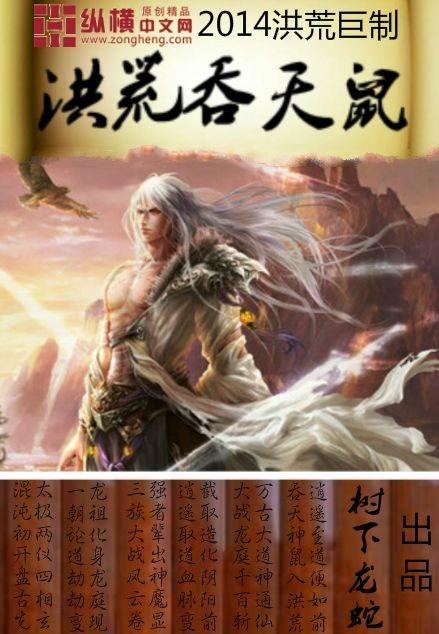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冰川期的动物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正寻思间,忽听“汪汪”几声狗叫。她更觉诧异,又听任远的声音在说:“来了,来了。”
罗如萱远远地叫道:“你怎么还没走……原来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那边任远说:“我骗你做什么?我真该走了,你也走吧。咱们楼下那车库里黑洞洞的,还是一道下去的好。”
罗如萱抛了倦意:“所以是你害怕,需要有人保驾下楼,对不对。”
任远只好说:“随你怎么编排吧,你到底走不走?”
罗如萱笑道:“走啊,不过,我要听你讲那小狗的故事。”
注1:check,修改程序时从存放源码的主机上调取程序,通常都有纪录。
那狗今年七岁半,按照犬类的年齿,怎么也算条老狗了。关于那狗的故事,任远讲起来并不那么津津乐道。狗比人更通人性,这也不是什么希罕事。任远也算是超脱了,但他的心远不是个秤砣,他每讲起这狗的忠心和深情,都难免会想起前两次婚姻。那两个姑娘,他都真爱过,但他显然已不在她们的速拨键里。是啊,自己在她们的记忆中到底留下个什么号码?一定不是什么幸运数字。
对人对己,任远都挑剔,他“一日三省吾身”,发觉近日来自己心理上变化微妙──再诚实地“省”一“省”,不对,哪里是微妙,简直是翻天覆地!那心底忽忽悠悠升上来的麻麻痒痒之感是从哪里来的?每天回到家,坐上沙发,闭上眼,眼前那些数码相片又是从哪里来的?相片上有爽爽朗朗的笑脸、或是恬静的脸、或是双眉微蹙沉思的脸,都是罗如萱的。他越来越喜怒无常了:见罗如萱笑了,他也高兴得了不得;哪句话说得罗如萱发嗔,他会深刻检讨自己笨嘴拙舌。他不由纳罕,如果一贯如此,自己不是早就成了社交大师,同事也不会送他个外号叫“沉默的羔羊”?他更是担心自己失去了逻辑──罗如萱越是要强,他越是想对她呵护备至。自己什么时候乐于“逆水行舟”了?自己什么时候成了“金州勇士”,竟然挺身而出,和“恐怖分子”拉姆兹近乎肉搏?自己不是一向独善其身的吗?他甚至觉得,罗如萱是朵绽放的鲜花,可望而不可即……可是自己也不是牛粪啊?
剖析已毕,他承认了,自己乱了方寸。乱了方寸自然有后果,他体会得深刻──“人贩子”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于是觉得丧失了安全感。他庆幸自己意识得早,亡羊补牢,在心的周遭又多加了几层篱笆,从此上班时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
罗如萱觉出任远的古怪,每到自己身边,就突然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她整日和电脑打交道,自然不是那么向往机器人。在公司里,郑丽娟已经渐渐成了她的知心朋友,下了班,两人常常一道去逛商场、喝咖啡,此外,教会里的活动更是排得满满的。和任远一起加班的那几天,她心中也潜滋暗长出一些异样的感觉,但任远忽然变得古怪,她一阵茫然后,再想想他还是个臭名昭著的“人贩子”,自己缤纷的世界里一定缺他吗?她于是耸耸肩,没有再多想。
天渐渐转冷、变短、多阴霾,硅谷的it产业依旧在谷底冬眠。其实年末通常是it界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季节,但今年年末,四海似乎都结了冰,生意上延续了两年多的低迷,加之要和伊拉克开战的预测几乎和现实一样真切,企业和百姓更是将银子深藏在地窖里。
商务软件业因为应用面广,潜在的用户众多,故而在当年it界初现颓势时,还被专家们认为有金刚不坏之身,经得起冰川期寒冷的蹂躏,但经济一萧条就是两三年,像vantaft这样不大不小的商务软件公司已经举步维坚。公司的上层决策者们一个个衣带渐宽,但彼此相对,既无同病相怜之感,更没有“我见犹怜”之情,无论是董事会上还是总裁会上,总有人拔剑而起,或是埋怨某总裁产品开发方向的决策失误,或是指责某经理一年前的哪个收购吃亏,或是嘲笑某主席哪项投资惨败,吵到最后,也总有某人遍体鳞伤而退。
vantaft的办公楼群里,下个季度又要裁人的流言传得太猛太滥,竟传成了流感,工程师中病倒了一片──他们都病在家中疯狂地往别家公司递简历,或是找熟人介绍工作,一有面试的机会,便立刻红光满面地去应聘。这样一来,许多产品的更新都被推迟,客户不耐烦,则取消了购买意向,成了恶性循环。
罗如萱倒是真的被传上了流感,这也归罪于前些日的连续熬夜。她休息了一天,觉得略略好转,便又赶来上班。她精疲力竭而成功地完成了enterprisepro的测试任务后,被马克安排给约翰打下手,还是搞质量保证。
约翰和拉姆兹截然不同,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写程序的功夫也过硬,但人无完人──实在地说吧,约翰远非完人,写的程序也远非完美。他今年四十好几,仍是未婚,但对异性孜孜以求。他其貌不扬,想不停地追慕为数不多的硅谷佳丽,难免要殚精竭力。有时他数周无红颜相伴,体内激素失去了平衡,人就像被狂犬咬了,四处找水找咖啡,嘴里“荷荷”有声,这个时候如果任务一紧,他写出的程序便也像是在四处找水找咖啡,乱无头绪;而一旦婵娟在侧,春宵一刻之后,他竟能陡然间脱胎换骨,头脑间似是壅塞顿开,思路清明,写出的码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让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