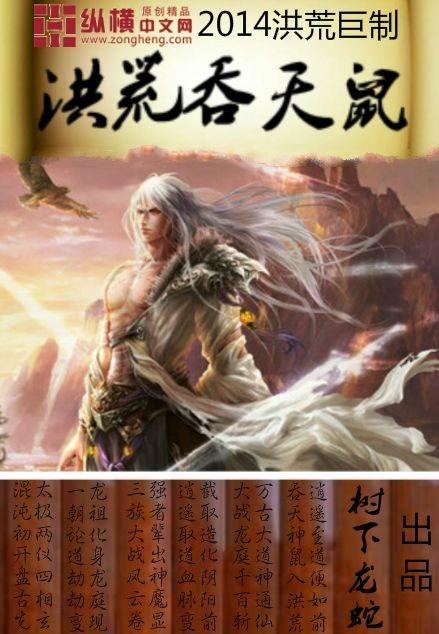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护士被杀案2020 > 第33章(第1页)
第33章(第1页)
罗尔芙护士长说:「她太忙了。病房里的两个二年级学生都得了流感。她让杂工给达格利什送了一张字条,大概是写了她昨晚的行踪。我看到杂工拿了进来,问我苏格兰场来的先生在哪儿。」
吉尔瑞护士长的语气变得气愤起来。
「话虽不错,不过她应该在这里。上帝可鉴,我们也很忙呀!布鲁姆费特就住在南丁格尔大楼,她和任何人一样,有可能杀死法伦。」
罗尔芙护士长平静地说:「她的可能性更大。」
「此话怎讲,更大的可能性?」
吉尔瑞护士长的尖嗓子划破了沉寂,双胞胎中的一个抬起了头。
「法伦在病房的最后十天,她把法伦紧紧抓在手中。」
「可是说真的,你的意思难道是……布鲁姆费特不会!」
「当然不会,」罗尔芙护士长冷冷地说,「所以你为什么要做出愚蠢而不负责任的评论呢?」
只有纸张的沙沙声和炉火的丝丝声打破宁静,吉尔瑞护士长坐立不安起来。
「我想如果布鲁姆费特再失去两个得流感的学生,她就会要求总护士长从这批学生中抽人了。我知道她已经盯上了伯特双胞胎。」
「那她会很不走运。这批学生的学业已经耽搁得够多了。毕竟这是她们毕业前最后的一段时期。总护士长不会将它缩短的。」
「我不敢确定,记住,那是布鲁姆费特。总护士长通常不会对她说『不』。有意思的是,我听说了一个传闻,说是她们今年不打算一起度假了。一个药剂师助理从总护士长的秘书那里听来的消息说,总护士长打算一个人开车去爱尔兰。」
我的天,罗尔芙护士长想,这里难道没有任何隐私了吗?但是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从坐在她身边的那个躁动不安的人身旁移开了几英吋。
正在此时,挂在墙上的电话响了。吉尔瑞护士长猛地冲过去接听。她又回过身走向那一群人,脸上堆起了失望的皱纹。
「马斯特森警官打来的电话。达格利什警司接下去要见伯特双胞胎。他已经搬到这一层的会客室去了。」
伯特双胞胎不发一言,也没有表现出紧张、不安,她们合上书,向门边走去。
4
半小时后,马斯特森警官在办公室里煮起了咖啡。会客室有一个小厨房,那是一个凹进墙里的架子,里面有一个水槽和塑料贴面的小柜子。柜子上有一台双灶头煤气灶。柜子里的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只留下四个大酒杯、一罐糖、一罐茶叶、一听饼干、一个大陶瓶和一个过滤器,还有三包真空包装的新磨咖啡。洗涤槽旁放着两瓶牛奶,奶皮清晰可见。马斯特森打开一瓶牛奶,先是不放心地嗅了嗅,然后倒了一些在平底锅里加热。他把陶瓶在热水龙头下冲暖和了,用挂在洗涤槽旁的茶巾仔细地擦干,舀取了很多咖啡,然后站在一旁等候壶里冒出第一阵蒸气。他很满意这些安排。如果警察要在南丁格尔大楼工作,这个房间的便利和舒适,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房间,而咖啡则是意料之外的招待,他从内心里把这归功于保罗&iddot;哈德逊。医院的这位秘书给他留下了能干而富有想象力的印象。他的工作也不容易。这个可怜的家伙夹在那两个老傻瓜‐‐济里和格鲁特‐‐之间,还得忍受总护士长的专横和刁难,他的地狱般的生活可想而知。
他小心翼翼地滤过咖啡,端了一大杯给他的上司。他们友好地坐在一起喝着,眼睛却瞟着被风暴摧残过的花园。他们两个都极其厌恶煮得糟糕的饭食和速溶咖啡。马斯特森想,他们只有在一起一边吃喝,一边痛骂小旅馆不合格的饭菜,或者像此刻一样一起品尝上好的咖啡时,才会变得更亲近、更喜欢对方一些。达格利什惬意地用双手握着大杯子想,玛丽&iddot;泰勒真是一个能干而富有想象力的人,能够保证他们喝上真正的咖啡。她的工作不容易,济里和格鲁特那两个无能的人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帮助,而保罗&iddot;哈德逊又太年轻,派不上多大用场。
津津有味地啜饮了一会儿咖啡后,马斯特森说:「这次谈话有点令人失望,先生。」
「伯特双胞胎吗?是的,我原本希望能听到更有趣的事情。毕竟她们俩身处秘密的中心。她们操作了那次致命的滴灌;她们窥见了法伦护士偷偷摸摸走出南丁格尔大楼;她们在半夜里撞见了正在巡视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但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获得更多的东西。」
达格利什在想这两个女孩的事。马斯特森在她们进来时准备了第二张椅子。她们并排坐着,长雀斑的双手按照礼仪放在裙摆上,双腿谦恭地交叉着,这两个女孩简直就是对方的镜子。她们对他的提问回以有礼貌的轮唱式回答,两人那种西部地区的沙哑喉咙听起来十分悦耳,和她们那阳光般的健康外貌一样令人愉快。他有点喜欢这对双胞胎。当然,他面对的可能是一对颇有经验的共谋犯。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她们有最好的机会在牛奶中下毒。和南丁格尔大楼里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她们也有机会在法伦临睡前喝的酒中掺入什么东西,这些都是肯定的。然而她们却似乎和他相处得十分轻松。或许因为要反复地重述她们大部分的故事,她们有点不耐烦,但是她们绝没有害怕,也没有特别焦虑,时不时还会以一种探究式的关切目光盯着他,彷佛他是一个棘手的病人,情况开始变得令人焦虑起来。在示范室和学生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注意到其他护士的脸上也曾有过这种热切而富有同情心的关注,但有点张皇失措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