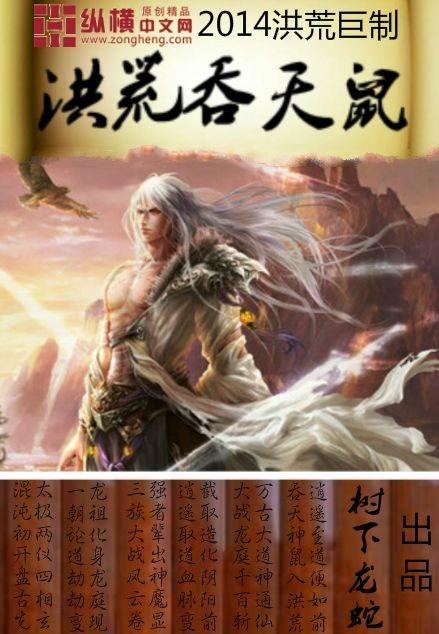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最强星座陀螺 > 085 目标东平王城二合一(第1页)
085 目标东平王城二合一(第1页)
“哗!!!”
伴随着水声响起,红云已是带着步野、柴宇靖跃到了一条宽达三十米的河流的水面上。
河中水流甚急,水也很浑,完全看不出有多深,当红云起跳的一刻,步野的心是真提到了嗓子眼上。
然后,红云就在那湍急的水面上奔跑起来。
红云四蹄下的云气形成了一个神奇的气垫,它每一脚踏下,并不是真的踩在了水面上,而是踩在了那个气垫上。
步野在红云背上向下看去,便能看到红云蹄下甚至连水花都很少浅起,只在身后留下一条长约两米的波浪。水流不停地冲消红云流下的波浪,而随着红云的奔行,又有新的波浪出现在他们身后。
步野颇为感慨地向河的上游望去,完全能感觉到那巨量的河水所携的源于大自然威势,由远处的天边而来,一直流到他们脚下,又流向天尽头。可是,在红云的四蹄映衬下,那份量真不知轻了多少。
上天造物也有所偏爱,云马,显然就得到了这种偏爱。
牧原城早有骑兵追了出来,但是坐骑全是龙犸和普通马匹,一直都追不上红云。而随着这条河的出现,不用绕远过桥的红云更是一举扩大了优势。
一个小时后,当红云在一个小土丘顶端的树下停下来时,步野心中已经只剩下“路遥知马力”的感慨。
步野先将柴宇靖丢下马,然后自己也跳了下来。
红云这个时候也不挑食了,直接就找土丘上的野草啃了起来。从昨天晚上碰到魏行那会它就开始跑,一直马不停蹄地跑到现在,它早就累了饿了。
步野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还昏迷不醒的柴宇靖,忍不住皱了皱眉。
其实在出了城门后柴宇靖就已经没了利用价值,如果要杀他,半道上步野就可以杀了,而不用带到几十里外的这里。
步野又看向了柴宇靖双腿,虽然伤口有几个,也流了不少血,却全都不深。那些敢于冒险刺向步野的士兵目标终究不是柴宇靖,当他们发现要误伤柴宇靖时,全都紧急收了手。客观地讲,柴宇靖腿上的那些伤口其实全是步野把他抡起来,主动在那些兵器上撞的……
无论如何,柴宇靖还不会因为这些伤死掉。此时昏迷中的他脸色很苍白,连眉头都锁着,应该是这辈子都没吃这种苦头。
步野可没多少时间,他摘下了腰间的水袋,拔开塞子,然后直接对着柴宇靖的脸倒了下去。
“哗啦啦……”
终于,柴宇靖先是眼皮跳了跳,然后睁开眼来。
双眼恢复清明的一瞬,他猛地从地上坐了起来,一眼就看到了步野。这个牧原城最风流儒雅的二把手此时脸上全是水渍,还粘着草屑,看起来已经有了几分孔乙己的风范。
“别慌,我还要问你几句话。”步野坐在那里根本没动地方,语气平静地道。
柴宇靖微微一怔,而后那全身的戒备劲一下全没了,也可以说,他整个人的精气神全没了。他甚至都不用去打量周围的环境,只看步野说话的状态,他就猜到了一切:步野已经带着他逃出了牧原,而他只有死路一条。
既然死已注定,那又何必再自乱阵脚,死都让人笑话?
柴宇靖松垮垮地坐在地上,仔细地打量着步野,然后自嘲一笑,感慨道:“我和玉哥儿一路摸爬滚打,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凶险还要更胜上几分。至少有三次,我们兄弟二人都只差一点就栽在别人的阴谋中。到了现在,玉哥儿和我共治一城,再往上便是只有萧家人才能做的郡王,非我二人所能染指,可以说,我二人已是位之极矣。”
步野笑了笑,冷嘲道:“你这是在变向的夸我?”
柴宇靖摇了摇头,不屑地道:“你只不过是一介莽夫,有何夸赞之处?”
“那你们却死在一介莽夫手里,又有什么好自夸的?”步野继续嘲笑。
柴宇靖一滞,这才想起来步野也是个擅长斗嘴的,昨天中午在刑台前他就已经有过体会。
柴宇靖苦笑了一下,悠悠叹道:“像我们俩,最怕的还真就是你这种不按规矩出牌的。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给我们造成威胁。”
这话步野爱听,索性顺着柴宇靖的话由衷道:“若是按规矩出牌,就只剩下死路一条。陆器抓我时,按规矩我不能反抗;反抗完杀了人后,按规矩我该有多远逃多远,任你们想拿多少村民开刀就拿多少村民开刀,我只能不闻不问;而我偏要问了之后,你们依然强硬地杀了人,按规矩我该认识到自己没被你们放在眼里,有多渺小,更该有多远逃多远,一生隐姓埋名……而你们,则只需让手下办事,自己坐享其成。”
柴宇靖笑了笑,算是认可了步野的话。
这时,步野抛出了最终结论:“总之,按规矩就是你们稳赢,我稳输。我还跟你按个屁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