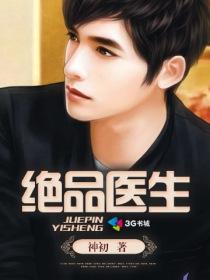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谋断九州地图 > 第五百五十二章 宠妃(第1页)
第五百五十二章 宠妃(第1页)
徐础回到谷中,受到众人的欢迎,得病的老仆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抓住徐础的胳膊上看下看,好像十年没见过面,最后道:“皇帝没赏给公子什么吗?”
徐础笑道:“皇帝的召见就是最大的赏赐。”
“哦,也对,见过皇帝的人才有几个啊?而且我家公子更了不起,是被皇帝请去的……”
回到卧房里,张释清道:“皇帝给你出什么难题了?”
“咦,你怎么猜到的?”
“我是看出来的,一见面我就知道你有心事,别隐瞒了,说出来让我听听。”
徐础于是再不隐瞒,将严、兰两位编修以及皇帝的话大致复述一遍。
张释清听罢,第一个念头却不是此事有多么为难,“宋取竹什么人都敢用,对敌人的部下他也放心?”
“这是皇帝的本事。”
“嗯。你知道是谁害死皇后之父?”
徐础点点头。
“告诉皇帝真相不就得了?”
徐础没吱声,张释清等了一会,恍然大悟,“原来……你怎么回答的?”
徐础正要开口,三个孩子推门跑进来,一个接一个扑来,抱住徐础的大腿叫父亲,最小的一个无腿可抱,蹦跳着去够他的手。
大些的孩子七岁,一个是徐础的长子徐埙,一个是田匠与冯菊娘的女儿田熟,两人一块长大,对娃娃亲尚还懵懂,见到双方父母却都用同样的称呼,经常为谁年长几天而争吵,小的一个刚刚四岁,是幼子徐篪,天天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后面,有样学样。
哄走三个孩子,徐础向妻子道:“我对皇帝说,‘当时便不知情,事隔十几年,回忆往事更是如隔重重云雾。’”
“回答得很好,可皇帝不肯放过你?”
“嗯。”徐础叹息道。
“皇帝究竟是怎么想的?让你为他证明清白?借你之手除掉郭时风?严微与兰若孚又是谁的人?”张释清越想下去反而越糊涂。
“等等再说吧,我想置身事外,怕是难得如愿。”
“贵为天子,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非要拉你下水?你已退隐多年,没参与大楚定鼎啊。”张释清抱怨道。
徐础的确不能置身事外,回谷的第三天,邺城来人,宣召徐氏夫妻一同进城。
张释清十分纳闷,“我又不认得皇帝,为何召我?”
到了邺城才知道,要见徐础之妻的人不是皇帝,而是皇帝带来的宠妃。
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种殊荣,张释清虽不情愿,还是独自前往行宫。
徐础住在谭无谓府中等候。
皇帝一住十余日,谭无谓终于能得些空闲,当日正好在家,邀请徐础到书房饮茶聊天,讲述天恩浩荡,“古语有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当今天子却非如此,重用功臣而不疑,历朝历代可有这样的明君?”
徐础笑着摇摇头,打定主意再不劝人。
聊来聊去,谭无谓道:“九州虽然一统,天下尚有不识时务、负隅顽抗之辈,陛下将要继续征伐,请我出任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