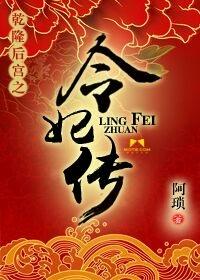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美人皮下 > 第12页(第1页)
第12页(第1页)
白皙的手指,暗黑的夜,孔雀蓝的烟盒。他将嗓子中暧昧软糯一口气缓缓吐出。颜秾则慢条斯理地开始卷起另一只烟,脚尖儿紧绷,随着某种节奏一翘一翘,她低沉的嗓音哼着一首歌——“i’veseentheword”“doneitall,hadycakenow”“diaonds,brilliant,andbei-airnow”正是那首《youngandbeautiful》——我看尽繁华,尽失初妆,纸醉金迷,历经沧桑……当我年华老去,容颜不再,你是否爱我如初;当我一无所有,遍体鳞伤,你是否爱我如初。“噔”的一声,颜秾打亮了火机,她右手举着打火机凑近烟头,左手拂开碎发。一星火苗在湿热的房间内燃烧,橘红色的星点摇摇欲坠。淡淡的烟味夹杂着微咸的水汽在屋子里弥散开。她将银亮的火机“哒”的一声合拢了盖子,随手抛在床上,重新抬起头,淡淡地凝视着他的双眼。他的眼被火苗灼了一下。她轻笑一声,细长的双腿分开,白皙的脚掌踩在地毯上,脚步轻悄。她站在他的面前,左手捏着那枚金丝点翠的烟盒,手臂横在胸前,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住细长的烟身。她夹着烟,手臂举在耳旁,俯下身,凑近他。空气几乎凝滞。她张开嘴,缓缓吐出一口烟。雾蒙蒙的烟气在灯光下像是一张透明的网,向着他的脸罩去。他闻到了她口中的味道,烟草的辛辣带着一丝清甜,还有丝丝缕缕玫瑰的香气。他的嗓子似乎被毛茸茸的烟丝划过,痒的厉害,口舌生津。他背部的线条发生了改变,整个人紧绷起来。她眯起眼睛,轻轻嗅了嗅上升的烟气,神情迷醉。她的美貌是一场盛世的纸醉金迷。她将手中的烟盒递去,那里面只装了一只烟,她做的手卷烟。白一茅低下头,看着她大拇指摩挲着点翠烟盒,烟气朦胧,他仿佛看到她的指尖也被染上了孔雀蓝。他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接过烟盒。白一茅无声一哂,打开烟盒,叼住烟卷。他果然没有闻错,烟丝中就有一丝玫瑰的香味,想必这烟也是清口的。他的大拇指和食指摩挲着烟卷,似乎上面还残留着卷烟人的温度。颜秾突然抬起双手,按住了他的双肩。白一茅惊诧地睁大了眼睛,却因为周导还没有喊“咔”不敢随意动作。颜秾推倒他,他的背部撞上假墙,一脚踏在飘窗上,一脚还踩着地面。她双膝跪在飘窗上,双手按在他身体两侧,她凌空的上身下是散发着朦胧光线的圆形灯。暗黄的灯光照亮她温暖的肌肤,凹陷的腰肢柔韧如水。她凑上前,橘红色的火光凑近他的烟头,她的双唇一抿,轻轻吸了吸烟嘴,烟头星火更亮。烟与他,一点即燃。作者有话要说:美人皮下,荷尔蒙的情话。颜秾的动作刚刚好,将他的脸推到摄影机拍不到的位置,只留下他紧绷的小腿,和一截烟身。她稍微后撤一些,两点火星在黑暗中燃烧。白一茅盯着她,咬紧了烟嘴,无论是潮湿闷热的室内,还是缭绕不断的烟味,都让他躁的很。周寒山猛地喊道:“咔!”颜秾跳下飘窗,将浴袍重新系紧。周寒山低着头翻弄着机器,呼气不平,良久才哑声说:“可以,过了。”站在一旁默默无声地阮钦拍了拍手掌:“一条过,恭喜恭喜。”颜秾礼节性地笑了笑。“还要补一个空镜头。”周寒山背对着白一茅无情说:“就不需要替身了,只要阿秾的手出镜就好了。”颜秾点头,并按照周寒山的要求,躺在床上,手指抓紧床单。周寒山却左顾右盼:“我的刀呢?阮总?”阮钦轻咳一声,将手中的道具刀奉上。周寒山趴在床位,昏暗的镜头中,一只白皙的手揪紧紫色床单,镜头上移,入境的是搁在果盘里的一把弹簧~刀。顿了顿,周寒山才喊了一声“咔”。颜秾坐起身:“还需要再来一次吗?”周寒山说:“床上这个戏……”话未说完,就听门口“咔嚓”一声。“别推,别推啊!进去了!进去了!”门“哐”的一声撞到了墙壁上,乔文整个人栽了进来,孟依岚、季深深和邵嘉全都压在他的身上,几人摔成一团。梁行渊双手插在兜里站在最后,他无辜地耸肩:“我劝过他们了。”合着他们全都趴在门口偷看偷听呢!周寒山大怒:“滚!通通给我滚蛋!明天早上都给我早起,去补给船上抬东西去!少一个,呵!”他大步迈过横在门口的乔文,头也不回地离开。阮钦信步跟在他的身后,也从乔文身上迈了过去,冷淡说:“那你们加油了。”好的,投资人爸爸。是的,投资人爸爸。“颜姐,咱们回房吧?我有些演技上的细节要请教。”孟依岚挽住颜秾的臂弯,朝刚爬起来的乔文得意地扬了扬眉毛。乔文咬牙。好男不跟女斗。所有人一哄而散,只有白一茅还留在屋内,他仍旧保持着方才的姿势,一脚踏在飘窗上,一脚踩在地上,嘴里还叼着那根手卷烟。白一茅抬起头,喉结不安地抖动,发出一声干渴的叹息。直到他将这一支烟抽完,才穿上衬衫,收拾起房间,他将所有道具摆放整齐,忙忙碌碌不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身体和头脑冷静下来。等一切收拾妥当,他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公馆内可供使用的房间有限,剧组人员都是两人一间屋子,二楼以楼梯为界分为东西两边,各三间屋子,白一茅跟副导演邵嘉住在西边第一间,周寒山跟编剧季深深占据了西边中间的一间屋子,而大老板阮钦则一个人住楼梯西边第一间。东边的房间从靠近楼梯这边开始,依次是拍摄用的屋子、梁行渊和乔文的房间,以及颜秾跟孟依岚的房间。白一茅进屋后,屋内无人,只有浴室传来“哗啦哗啦”的流水声。白一茅坐在床上,背脊因为多年的习惯依旧挺得笔直,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已经不在军~队了,随即吐出一口气,弯下腰脱鞋。无意间,他的眼神瞄到了床上摊开的剧本,上面写着这样一段——陈喃迅速冲上前,一拳打上欧放的脸,欧放摔倒在地,随即跳起,也一拳揍上陈喃的脸。白莺惊恐地看着。白莺:你们在做什么?!陈喃与欧放扭打在一起。白莺面露嫉妒。白莺:你们疯了,就为了一个女人!“就为了一个女人。”白一茅喃喃念出这句台词。他心烦气躁地抓起床边的烟盒,叼着他以往常抽的烟,却怎么品怎么不对味儿。他随手将烟盒抛到一边,拉了拉衣领,他的电话在这时响了起来。白一茅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又扫了还在“哗哗”作响的洗漱间一眼,他拿着电话,站在窗边。窗外的是一片能将人吞噬掉的黑暗。白一茅接起电话。他轻声说:“我这才刚上岛第一天你就来电话催,你可真给我找了个好活儿啊,我他么的都给人作裸~替了,这一辈子的脸都丢尽了。”“有没有好处?”白一茅重复着电话那头的话,身子靠着窗户,有些失神,忍不住低头一笑。他随即站直身子,淡淡说:“没有,你听错了,什么声音也没有。”那边不知道又说了什么。白一茅神情严肃起来:“我说真的,你把这个委托撤了吧,他们两个不是那个关系,我可不能昧着良心赚这钱。”“要赔钱?”白一茅沉声,“我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