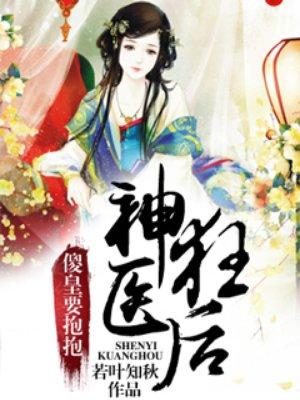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有恙拼音 > 第46章(第2页)
第46章(第2页)
父亲咳嗽了声,风箱的鼓动也停止了一瞬:“于情于理,不该等我死了再回来么?”
“我比你有良心。”司望说,“总归不会把你逼到绝路。”
“你们一个个的,翅膀硬了,把你们养大倒成我的不对了。”父亲说,语速很慢,但他仍然坚持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长句子。
司望也有时间,等待一杯热水冷却,再慢慢喝下。
“那照你这个逻辑,我花钱把你救回来,是我的不对。”司望捏着纸杯,看着里头小小的湖面,倒映一盏小小的人工月亮。
昏黄,黯淡。
明天有时间,他还得把电灯泡换了。
“我也没心情跟你争论是非。”司望说,“你怎么都是有道理的,我怎么都是没道理的。”
“明天我会给你再找个保姆,你要自己能动弹,就别使唤我妈。”
他这次回来,也不是为了跟父亲吵架,他认为他从来都没有跟父亲吵过架。
他们隔得太远,打电话都听不出彼此的情绪。
至于回家当面聊,抱歉,他工作忙,非常忙。
他忙着赚钱养活父母,也忙着向弟弟妹妹求取原谅。
同时,忙着习惯苏白的离开。
而父亲总对于儿女们有着过高要求,希望司望能兼顾事业家庭无所不能,希望司宇能乖乖听话嫁个有钱靠谱的alpha,希望司源从婆家拿钱回来最好每个月有固定的打款。
他在骄傲地等待儿女们的报答,可儿女们则在倔强地等待他的道歉。
不,连道歉都不奢望了。
只是没能狠心到让他自生自灭。
母亲,还有母亲。
司望该是舍不下她的。
但司望也确实对她没有太深的印象。
十五岁前的司望安静、懦弱、迟钝,存在感稀薄,与比他存在感更薄的司源在外边玩一下午,都不会有人发现他们兄妹俩消失不见。
母亲更中意司宇,这个一出生就伶俐漂亮的小娃娃。
再者司宇司源一出生都是跟着母亲,只有司望跟着爷爷奶奶长到六岁,才被接回县城的家中。
母亲对爷爷奶奶家的东西一向不喜,土豆红薯,南瓜白萝卜,碍于父亲的脸色没法把这些乡下来的特产扔掉,只能做饭的时候念念叨叨,说这个长虫那个打农药了不健康。
对于司望也是一样,只不过碍于他是她身上掉下的骨肉,没办法真正扔掉。
随着司望的长大,母亲对他愈发的客气小心,似乎在害怕他的报复。
可他都不回来了,远隔千里,但她连叮嘱注意身体的话语都只是附和父亲的无理取闹。
司望因此差点中暑过一次,在l市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苏白还笑他听话到犯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