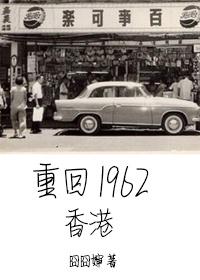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富豪游轮变屠场 > 第214章(第1页)
第214章(第1页)
斯库文爸爸为他保留了更好的东西。更干净的东西。
他暂时抛开失败的念头,给自己开了一个独特的离别晚会。
一个当地的女孩在河边洗衣裳。他们互相微笑。嗨,我是特里弗医生。小甜点心。
她光滑的躯体在凝脂般的绿色丛林的静寂中散发香气。
他用她的洗衣篮子打来河水冲洗她。他把她留在大树底下。
他的又一次表演。
再见了,粪坑。
在阿姆斯特丹逗留数月。那些妓女。他倒是愿意和她们进行一次真正科学的表演,可是没有时间。
回到家里,他到医院里医生办公室去找他。老杂种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嘲弄的眼神望着他,好像在不屑一顾地说,看,我说过会这样的。
你得再给我找一个学校。一个真正的学校。
噢,当然,就跟这所一样。
那你就试试。他知道这老杂种的把柄在他手里。
但一星期后,这老杂种就作古了。他死在手术室里,就倒在一个病人的身上。
这可真是第一流的笑话:一个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死于心脏病突发。整天忙着清理别人的管道,以此大发横财,而自己的却被墙死了。
可笑,但并不可笑。到死,这老杂种还狠狠咬了他一口:他没有被列在继承人名单之中。一切都留给了莎拉。
好像她会需要它。毕业于哈佛,一个精神病医生,刚在波士顿开了一个诊所。又和那个矮胖的长着鹰钩鼻子的小杂种结了婚。尽管他是一个胆小鬼。但重要的是,他家他妈的真有钱。这两个人在忙着嫂罗财富,在贝肯山上有别墅,在海边有度夏的房子,衣着华丽,出入高雅场合。
他和莎拉在葬礼上几乎都没有认出对方。他盯着她的乳头,保持沉默,和谁都不说话。她把这种表现解释为极度悲伤,给他写了一封信,深表同情,言辞热情而恳切,把那所粉红色的房子转送给了他。
给愚蠢的小弟弟一根骨头。
有一天他会为了这事杀了她。
他掌握的医生的把柄已经没有作用了。他重新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处境:他拥有他的车子。他的全部有价证券也还不错‐‐尽管只有几百元。存款帐户上还有四十二元‐‐那是他历年来认医院的工作中靠私自出售药品攒下来的钱。他的衣服。图书室中的藏书。那本大绿书。斯库文圣经。装在天鹅绒皮套中的刀子。
他以很低的价格很快把粉红色房子卖掉了,这又进账了四十万。交完税后,还剩下二十三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