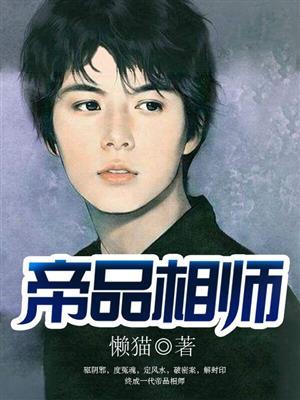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君子之交全文番外 > 第132页(第1页)
第132页(第1页)
分开的十几年里,他还在演那个男人心中的任宁远。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他答应过那男人,要惩罚那个强暴犯。都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没有什么是他任宁远无法忍受的。而那人日后即便成了丈夫,成了父亲,将来成了祖父,也能日复一日对他念念不忘,憧憬不已ii他想,这就是他最好的成就。这世上的感情,唯有保持距离才能永不腐朽。然而有一天,那男人带着女儿来了t城找他。然后一切都不一样了。那些日常幸福里的阴影,只有他看得见,那男人因为无知而幸福,他就尽力地,让那男人幸福地无知下去。撒一个谎容易,却需要越来越多的谎言来弥补。那男人对他的信任和仰慕一天天长大,危险的脓疮就一天比一天可怕。他演了十几年的英雄,也轻微的觉得疲惫,终于积累下来的真相到了爆发的时候,他还不死心,他想弄清楚事情究竟到了哪一步。他问曲同秋:「你知道了什么?」男人颤抖着说:「我不想知道了。」于是他知道,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男人说:「我会回去的。」不可能的,回不去了,谁都不能回头了。他不能让他一个人逃走,然后把他独自留在这里。「是我。曲同秋,那个人是我。」在那认罪的一瞬间,他竟然也有了一丝的轻松。男人疯了一样挣扎,朝他脸上用力「呸」了一下。在他一手制造出来的美好世界彻底裂开坍塌的时候,他也觉得全然的解脱。他终于,可以不用再扮演了。天都破了一个大洞,大雨倾盆,他也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也许会有阳光,他从这废墟里,能捡起什么东西。他把情绪失控的男人软禁起来,终究也不是办法。庄维一直在跟踪他,誓要把那男人找出来,楚漠告诉他「你就是他的病」,连苏至俞都说男人已经疯了。他习惯了自己的无所不能,对着那个男人却无能为力。曲同秋一口咬在他脖子上,只用牙齿就几乎咬断他的颈动脉的时候,他突然清晰地感觉到这男人有多恨他。这种刻骨的痛恨,几乎和当年的仰慕一样深。而他甚至想不出半点办法来让那男人好受一些。他因为失血过多在医院里待了一下午,曲同秋就已经成了庄维的了。这世界,每一分钟的变化,他都无法把握。他知道庄维会对那男人做什么,庄维不像他,庄维只很肆意地作一个凡人。他想象得出全无抵抗能力的男人被庄维玩弄的场景,而他动弹不得。这世上现在只有他最没资格说「请对曲同秋好一点」,因为他自己已经把曲同秋毁了。他连觉得痛苦的资格都没有。终于庄维也松了嘴,同意让他带着曲珂去和曲同秋见面。他一对曲珂说「妳爸爸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曲珂就欢欣雀跃。他到现在还记得他们俩那时候充满希望的快乐。曲珂立刻就把丢在那里搁置了好久的围巾捡起来,废寝忘食,只用了一天就织得差不多。可惜临时抱佛脚,功力毕竟还是不够,到了收尾部分就卡住了,她不会收针,总不能那么无穷无尽地织下去吧。「好吧,那就小小作弊一次。」任宁远带上她去裁缝店,让人帮着把边都织好了。完工的围巾虽然有一两个小洞,不细瞧的话还是很好看的,曲珂一路都美滋滋地抱着,吃饭的时候忍不住又掏出来。「不知道我爸爸戴起来合适不合适呢,」光是想着就让她很高兴,「任叔叔你帮忙试戴一下吧。」他也笑着试戴了这条围巾,很暖和,他觉得那男人一定会喜欢。然而曲同秋却不肯见他们。等了几天只等来这个结果,曲珂几乎是马上就躲回房间里去了。他能明白她的伤心和失望。他也不知道是哪里又出了错,那男人明明是那么的疼爱她,也许那男人对他的恨,甚至都超过了对她的爱。关于那男人的一切,他都越来越无法控制和预料。人心真的不是他能掌握的。他每一天都觉得自己更无力。他想要的其实也不多。他只要那个男人一辈子都景仰着他,在他身边,为他做一份早饭。很多事情他都觉得可做可不做,不必太强求,只要老来可以相伴就足够。他和他的名字不可能一起出现在婚礼喜帖上。那么能一起出现在墓碑上,也是种安稳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