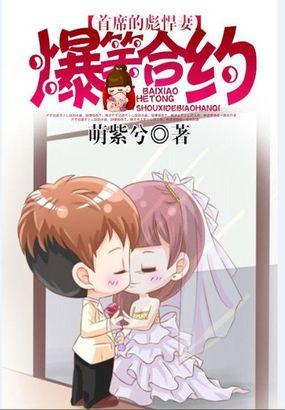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女司机上路 请注意 > 第30页(第1页)
第30页(第1页)
直到她听到邬童买一张沙发都能花掉三十七万。第一任丈夫的抚恤金也只是十五万。她存在账户里,从来没敢碰过。她总觉得那是他化成了一串数字,静静地躺在那里,陪着她们母子。她以为这串数字会跟着她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直到变成一个更大的数字、再变成一处坐落在这个城市的房子,继续守护着他们的孩子过下去。现在她知道了,这串数字和她这些年的努力,连一张沙发也买不来。她的车在一处炒粉摊位前停下了。老板和她早已有了某种默契,什么都不用说,就隔着车窗递过来一盒火腿青菜炒粉、两罐啤酒。“方教练,我看到王槑今天钓到鱼啦!你们家老太太开着窗户炖鱼呢,今天还在外面买着吃呀?”有熟悉的邻居问。方一楠疲惫地笑笑,什么都没说。她带着那盒炒粉和啤酒,驶向了另一条长长的巷子。2王槑的母亲,巷子里人称“两把刀”,一把刀是她嫁进王家时剁在准备给她下马威的婆婆面前的,另一把刀是她夜半时分去李寡妇家薅王槑父亲出来时抄在手里的。年轻时,她脾气暴,扫了一辈子的地,这脾气也变了,对内不对外。对王槑和王槑的父亲,她依旧是日日里横刀立马;对方一楠和方一楠带来的那只“拖油瓶”,她一般采取的是笑里藏刀的方式。这个晚上,开着窗户炖鱼是假,躲在巷子阴影里看方一楠到底和谁见面是真。对于方一楠和王槑的结合,她一直认为另有猫腻。“王槑有什么本事?啊?什么都没有。这个儿子随你,我跟你讲,他十八岁那年我就把他看明白了。不会有人真心待他的,除了我这个给你们爷儿俩当老妈子的,没人了。”二把刀曾铿锵有力地对着王槑的父亲下过这样一个结论,“她带着个儿子嫁进来,图什么?就是图你儿子那套破房子。不要不相信!一旦拆了,那就是几百万。”在她的坚持之下,方一楠和王槑没有领成结婚证。她笑眯眯地敲打着方一楠:“你们大男大女的,领不领证只是一个形式,住在一起就算结婚了。我们那个时候都这样,有事实婚姻就行。什么证不证的。”她时常担忧方一楠会从王槑身上剋下什么钱来,毕竟王槑的钱就是她的钱,这个家里所有人的钱都应该是她的钱。她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格去替王槑“管着账”。在方一楠洗澡的时候、去厨房做饭的时候、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她都以突击的方式查看过方一楠手机里的消费账单。在那些本就稀少到令人心疼的消费里,她发现方一楠每天傍晚都会去买炒粉,而这些炒粉从来没在家里出现过。“她有人了。”二把刀忧心忡忡地对王槑的父亲说。王槑的父亲正拿着小本子记录收音机里听到的彩票号码,对这句话不置可否。“给我看着鱼。”二把刀叹了口气。王家父子没了她果然不行,她想。3在方一楠走进家门五分钟后,二把刀也回来了。她脸上有一种隐秘而快乐的神情,尽管身高不到一米五,她依旧居高临下地环视着家里每一个人。“妈,你有话要说?”王槑问。二把刀神秘莫测地笑笑,什么都没说。她只是以一种非常怜悯地、宠溺的眼神瞥了一眼王槑,提醒他擦擦吃饭热出来的鼻涕。她高昂着脑袋,轻轻走回自己的卧室。她相信儿子很快就会痛哭流泪地回到她身边,发现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信的、忠诚的女人只有她。在他们家那间出租屋旁,她亲眼看到方一楠把炒粉递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上个月才来的房客,是在建筑工地打工的,看起来岁数比王槑他爸还要大几岁。“她图什么呢?”躺在窗边油光水滑的竹椅上,二把刀百思不得其解。4“新来的那个房客,可怜得很。”王槑坐在他和方一楠的那间侧卧里,像虾米一样弓在书桌前。他在研究他的那些钟表——要说王槑还有什么需要花钱的爱好,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迷恋旧钟表。床头那一整面墙都挂满了他在旧货市场淘来的旧表。黄铜的、祖母绿的、玳瑁的、银色的……那些代表着时间的齿轮紧紧咬合在一起,它们不会再走了,却让王槑感到迷人非凡。他有时能盯着它们看上一两个小时。方一楠坐在他身旁,时而给他递上一把小小的钳子、镊子。她对这些微小的机械不感兴趣,她只是觉得王槑想让这些钟表再次走起来的想法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