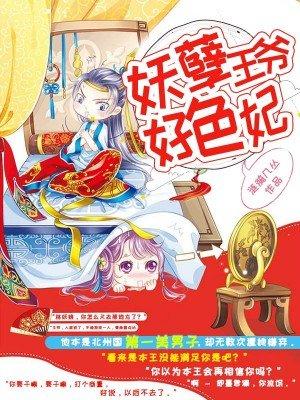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4、表哥见我多妩媚 > 第49页(第1页)
第49页(第1页)
有说不出的情感,流遍他的周身。让他想拥抱知知,想亲吻知知,想整夜整夜地陪在知知身边,再不要离开她半步。他想化成她发上的簪子,可以每天被她插在发上;他想化为她手里捧着的竹简,让她垂头读书时,每日每夜地看到自己;他想化成妆镜,让她揽镜自顾;他想化成她天边的明月,千里相随相伴不舍不弃。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他从来没有这样在过后的一个时辰内,越想越开怀,越想越羞涩,越想越想冲回去,再死皮赖脸地央求她!她轻轻碰了他脸颊一下,而一股热流,便从他的滚烫颊面开始,蔓延全身。他的五感丧失,他的理智沉沦。他就此不复醒!十五岁的李信贪恋着这种奇妙的感受,他如此敏感,他时时不能忘记。他感情炽烈,情绪激烈。也许他这一生,也只会在这个时候最渴望一个少女的感情。明明知道她凉薄,明明知道她和他云泥之别,可是他拼尽全力,也要去争一把。闻蝉亲他一下,他愿意为她去死!无怨不悔!她让他变得这么冲动,变得这样不计后果。他曾经计划,而他现今渴望,幻想。那样愉悦的快感,让李信觉得,这是他值得一生去追求的。李信身份低微,然他内心骄傲。他对自己定位清醒,他明确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未来要怎样。如果没有遇到闻蝉,他会成为山大王,会成为会稽的地下头领,会是这片地域的隐形王者!李信自我而强势,他从不为别人而活,他做什么,永远只凭自己高兴。……而现在,让他最高兴的,就是闻蝉了。李信忽而一跃而起,动作如残影般向上斜掠,攀附树木,上了树,又在树上一弹,跳上了高高的墙上。他喜欢站在高处,他站在皓雪墙头,看着郡守府的方向,看那处灯火熹微。风吹来,雪满身,李信放声大笑,笑完后,眸子更加亮,伸出手,在半空中,圈出了一个小小的轮廓。李信轻声道,“我一定要你!”他算着自己留给闻蝉的东西,算着如何感动闻蝉。闻蝉的感情,需要他一步步算着来。然即便将这些都想一遍,胸臆中的燥热仍无法缓解。李信身子忽然往后一仰,从墙上往下跌去。他双手枕着后脑,摔躺在了雪地上。雪飞溅,雪灌撒,他整个人,被埋入了厚雪中一般。然即使是这种冷冽,仍无法让少年冷静。他满脑都是闻蝉,都是少女的一嗔一笑。他不用闭上眼,她都能自动跑到他脑子里来。“女人啊……”李信嘿嘿笑两声,从地上跳起来,抖了抖一身雪。三更半夜,少年阿南躲在陈朗之前的家里睡觉。有雪在外面簌簌飞,晚上早就关了窗子。虽然没有炭火,屋里仍然很冷,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居无定所的混混来说,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阿南酣睡。酣睡中,突然打个哆嗦,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冷意。阿南反应很快,立刻睁眼,躬身要动手反拿来人时,来人与他快速地交了几次手。看到少年带着一身雪粒子,蹲在木板外,阿南先是松口气,然后又快疯了,“阿信?!你半夜来找我干什么?还吭都不吭一声地蹲我床头,吓死我了!”阿南揉着惺忪睡眼坐起。屋子另一边,少年李江听到了深夜中阿南的说话声。他蹑手蹑脚地下床,靠在门后,看到是李信,眸子闪了一闪,没有进去。李信根本不在乎那些。他就蹲在阿南床头,很严肃、很正经、很认真地跟阿南说,“我想女人了。”“……!”阿南的瞌睡,一下子被李信的神来一笔给震飞了。他呆愣愣地看神色平静、满身飞雪的李小郎半天,突然揉着下巴,扫一眼李小郎的样子,乐不可支。儿郎之间,一谈起这种事,就特别容易拉近彼此的感情。阿南半夜被李信吵醒的恼怒,一扫而空。他高兴地搂着少年单薄的肩头,怂恿道,“这么晚了……咱们去娼家听听小曲去?”他冲李信眨眼睛,神情暧昧:男的嘛,都懂这是什么意思。李信笑了。有些跃跃欲试。不过他现在满脑子想到的女儿家,只有一个叫闻蝉的小娘子。除非让他立刻能睡到闻蝉,不然他对别的,暂时还没有兴趣。很久以后,当少年李信长大,他会明白,一开始定得太高,那天下大部分女人,在他眼里,都会变成庸脂俗粉。世上再没有一个在他少年时、就走入他世界的知知了。李信扯阿南起来,“跟我出去,咱们打一架!”阿南抱住木板哀嚎,“有病啊?!谁要跟你打啊?!不想去娼家,就给老子起开……阿信你放开老子!”两个少年推着打着拽着,拖起地上的尘土,骂叫着,很快就到外面的雪地里野去了。阿南任劳任怨地去陪李小郎散去他一身火一样狂热的激情。躲在门后偷听的李江,扯了扯嘴角,又回去睡了。他有时候很茫然,好像自己拼尽全力想做的事,李信却全不在意。他想成就一番大事业。李信却在想女人。……李信心里,莫不是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他?何等不甘心。而在屋外,李信和阿南打斗中,忽然漫不经心般随口来了一句,“我觉得那个李江,总是偷偷摸摸地不合群,不知道在忙什么。你多注意下呗。”阿南愕然了一下,看李信提过后就不再说了,挠挠头,随意答应了下来。心里想:李江?那个长得俊俏的小白脸?能出什么事儿啊。阿信真是想多了。不过阿信从来就东想西想想得特别多,也不管最后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少年们在雪地中如此发散过剩的精力。郡守府中,舞阳翁主辗转反侧,睡得很不安稳。梦里,总是不停闪现李信洋洋得意的、狂傲不羁的、又平凡得没有一点特色的脸。她又无数次回到之前的一个时辰,回到自己鬼迷心窍,觉得他特别好玩,就情不自禁去亲他脸的那一刻。她疯了。如果让她再回到那一刻,她一定要牢牢把持住,不为他所动。但是这一个时辰,明明赶走了李信,明明夜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明明上了床入睡。可是不停地翻身,不停地心烦,而心跳,砰砰砰,在深夜中,跳得那么快,声音那么大。她在狂跳的心跳声中,面颊绯红,埋入床褥间,强迫自己入睡。“知知……”好像又听到少年在她耳边的坏笑声。闻蝉突得坐起来,手碰到了床前矮几案上,一个东西,在夜中,摔下地,发出清脆的声音。少女散发下床,赤脚踩在席垫上,探身去捡摔掉在地上的玉佩。少女捡起了一块玉佩,并玉佩下压着的一块粗布。玉佩的样式有些眼熟,让闻蝉怔了怔。她拿着手中的东西,一瘸一拐地挪向窗子的方向。没有点烛火惊起外头守夜的侍从,她站在窗子边上,就着白窗外照进来的透亮雪光,去看手中的东西。闻蝉认出了这块玉佩,是在徐州时,她在大街上挑东西,被李信抢去的那枚玉佩。再次见到熟悉的工型结构的玉佩,闻蝉怔了一怔,手握紧怀中东西:李信还留着这个啊。应该是之前她腿脚不便,又再不肯亲他,李信抱她上床后,看她闭了眼后,放在她床头矮几案上的。但是她又恍惚了一下,咬着唇:如果李信一直留着这个玉佩,那现在还给她是什么意思?要和她一刀两断的意思?她是该难过呢,还是该惊喜呢?闻蝉分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了。她低下头,去看李信留下来的粗布。她看到布上写着的字。飞扬无比的字体,顿笔处大概因为不会写,转笔转得很生硬吧。反正他那跟飞起来差不多的字体,和他这个人的感觉是一致的。闻蝉几乎能想象到他抓着她桌案上的狼毫,烦躁地写字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