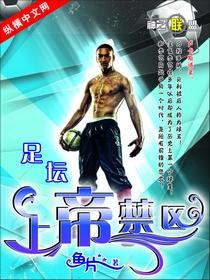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皇后她媚香撩人 作者丸子炒饭好看吗 > 第44章(第1页)
第44章(第1页)
她编出的理由并不足以叫人信服,端看圣上愿不愿意听信。
依苏笙现在的时而清晰时而混沌的思路,她圆不出一个完整的谎言,如果圣上愿意掩盖此事,只要她编出些理由,皇帝也就此不了了之。
圣上与东宫之间彼此尚且戴着一层温情的面纱,若教圣上知道自己亲立的储君私底下费心安排了这么一出,丝毫不在乎这是圣上母亲的忌日,恐怕还会后悔为何要查下去。
东宫知道圣人与自己的未婚妻有了几次肌肤之亲,难说会不会祸起萧墙,学着当年拥立圣上那样再谋算一场宫变。
“感业寺酷夏难耐,臣女以温水沐浴,应该便能消解暑气的。”沐浴能不能将体内翻腾的渴求平复她不清楚,然而圣上总不可能看着她沐浴更衣,趁着那时候苏笙才有机会把那些不该出现在佛寺的东西“毁尸灭迹”。
“圣人日理万机,臣女不敢耽搁陛下,想来宋司簿很快就会回来,此处就不劳圣人费心了。”苏笙没眼看圣上仍未消解的那处,“您若是想……臣女的意思是圣上乃是君王,若是想要恩施雨露,想来寺庙之外也有许多女子心甘情愿。”
英宗贵妃不知道是花在她身上多少心血财力,才将她这身肌肤养得如此莹白,却被苏笙自己这样毫不心疼地掐按,屋内无人侍候,圣上微微沉吟,他教坏一个小姑娘或许不是什么好事,但总胜过她自己这样不得章法地残害自己的身体。
男女愉情,他比起苏笙要更看得开些,这姑娘学了许多秘戏图,却也是懵懵懂懂,不知道其中的关窍奥妙。
苏笙感觉到圣上倏然的靠近,她心底并不厌恶圣上的亲近,不过还是后退了几分。
药效使然,她现在像是青楼楚馆的女子,甚至在渴求男子的靠近。然而这种亲近并不为礼法朝纲所允许,花无百日红,而她自己也要掂量清楚圣上的亲昵能维持多久,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同他有了首尾,等到宠爱尽失,还能不能全身而退。
“今日之事都是臣女的过错,臣女还请圣上准许,让妾入感业寺削发修行,为圣上祈福。”苏笙横下了心道:“若是陛下将臣女药哑或是赐死,臣女也不敢有怨言。”
那曾握过朱笔的手强硬地握住了她的手腕,苏笙苦笑了一声,她想倚仗圣上的一点慈爱仁和,以退为进,然而或许天家的父子都是一样的脾性,太子要鱼与熊掌兼得,圣上起兴之后也不会顾惜她的心意。
这里本就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圣上何须用那爱民如子的面纱遮掩,他想要的,必然可以得到。
他没有说好与不好,苏笙反抗不了太子,更加无法拒绝一位帝王,一切进行得沉默无声,但这次直到她软软地惊呼了一声,伏在案几上感受那份奇妙后,圣上也没有真正地将她怎么样。
皇帝用绢帕擦拭了手指,面上也带了微不可察的羞赧,他淡淡道:“番邦使臣常说天朝风气开放,朕却不以为然,你们这些孩子正处在最好的年纪,却古板得很。解决的办法又不止那一种,怎么遇上一点事情除了出家和自尽,就想不到第二条路吗?”
“臣女污了佛寺,受罚也是应该的。”圣上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苏笙是料不到的,然而她在感业寺行出如此不合佛法的事情,叫旁人知道也不得了。
苏笙看太子当时遗落在这里的手炉已经不再散发香气,这叫她心内略感安慰,她刚刚糊里糊涂地就到了极乐之境,只差将尴尬二字写在脸上,她提心吊胆,圣上倒对此事不在意。
“苏娘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不顾惜自己,难道佛祖就会原谅你吗?”两人刚刚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一时静默无言,圣上待她脸上的红晕消散,才对她道:“人命并非草芥,在佛陀看来,这些身外之物远不如众生一命重要。”
她的模样看起来并非出自本心,圣上自问他也不是教人害怕到能止小儿夜啼的程度,何必这样苛责自己。
“若要罚,就罚你在这里抄上一卷经书,明日送到主持面前。”
圣上瞥见苏笙的眼睛有意无意地飘向案上的香炉,与主持叙旧时他似乎在三郎的衣袖中见过一个十分相似的。
但有些东西却并不急在一时,今日的事情传出去,无论是在前朝后宫都会掀起千层风浪,太子妃失德,大概御史台也要上书求皇帝严惩不贷,三郎这个太子也做不安生。
可只要天子不愿意声张,这件事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苏笙正跪在罗汉床上,她没有想到皇帝会这样轻飘飘地发落了她,圣上多少嗅到了她身上的香气,应该也有些未曾消解的火气,然而苏笙担心了半晌,圣上却只是迟疑了一下,还是步出了这间静室。
元韶或许是以为圣上还会在里间停留许久,恪尽职守地守在院门外,生怕有人进来撞破了皇帝的好事,见圣人不到半个时辰的工夫便衣冠齐楚地从内走出还有些惊异,像是这等难得的人间春色,圣上骤然得手,正该如胶似漆,居然也舍得放下?
他暗自纳罕,却还是躬身向皇帝禀报:“奴婢叫厨房烧了热水,江掌衣也拿了新的衣裳供圣人穿戴,不知今日之事该不该请女官记上?”
“衣裳便不必换了,”又没成事,他在这处更衣做什么?
圣上的眉峰渐渐耸起,做到这一步,同幸了她也没什么区别,最后只叫人送了水进去,“留下一些人看牢了苏氏,她若是寻死,叫宋司簿多在她耳边提点两句。”